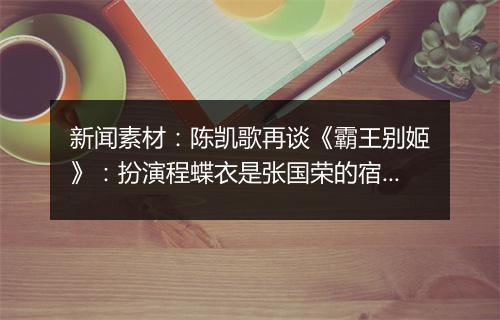新闻素材:陈凯歌再谈《霸王别姬》:扮演程蝶衣是张国荣的宿命
原标题:陈凯歌再谈《霸王别姬》:扮演程蝶衣是张国荣的宿命
日前,北京电影学院78级校友陈凯歌导演近带着《霸王别姬》回到了母校,在映后交流阶段谈到这部影片的缘起、剧本创作、选角以及给他带来的影响。
以下为文字整理实录,未获授权,请勿转载!
文字整理:张树铭
大家好!
再次回到学校,今天看到这么多老师同学们在场,感到非常的开心,虽然距离我入学已经四十年了,可是对这个学校,对这个地方,仍然有很深的个人情感,谢谢今天大家来。
光阴似箭,霸王别姬这部电影问世已经有二十五年时光了,当年参与拍摄的几百个工作人员,有些都已经不在了,还在的这些工作人员提起拍摄的那些事儿,都还和昨天一样,非常感慨。
我的两位非常亲密的合作者顾长卫老师、陶经老师,当年风华正茂,都是三十几岁的年龄,我的同校同届的同学,却创造出那样雄浑壮丽的声音和画面,很了不起。
张丰毅是我们七八级表演系的佼佼者,他所演的段小楼丝丝入扣,非常精彩。还有赵季平老师,我们从《黄土地》就开始合作,他一直是我尊重的作曲家。
还有谁呢?
还有很多,我的助手、合作者张进战、白玉,美术杨占家都对这个电影作出了很多的贡献。
我们这个戏基本是在隔壁北影的厂区里面拍摄的,也去了北京的很多其他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厂区所搭建的景地有些已经不在了,和那些人一样,有些还在,但是已经非常苍凉破旧了。
我现在到了那个地方,自己对自己说:“真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即令如此,我已生了很多关于无常的感慨,唯一留下来的,是这部电影,二十五年来,一直都在这。
——陈凯歌导演说
《霸王别姬》的缘起
《霸王别姬》这件事情的缘起是从一位住在香港的女制片人徐枫女士开始的。
徐枫女士原来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女演员,和胡金铨导演合作拍摄过很多经典的影片,其中有名的就是《侠女》。
七十年代的时候徐枫跟随胡金铨导演去过戛纳电影节比赛,那是当时华语电影得到的唯一一个技术大奖,从此徐枫女士便对戛纳电影节情有独钟,在电影节的时候经常去。
我就是1988年在带着电影《孩子王》去参加比赛的时候遇到的她。
那时候的两岸关系还没有后来那样的发展,我们见面之后说约个地方聊上几句时都挺紧张的,可见收录时间能把很多事情改变。
等到《孩子王》在戛纳的首映式这一天她也来了,影片放映完以后大家匆忙打了个招呼就散了,第二天她又找到我说:“你拍的挺好,但是我觉得你能拍的更好。”
她说我这有本书,你看看,愿不愿意把它拍成电影。我当时真没当回事,因为一个制片人将一本书交与一位导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本书就是《霸王别姬》。
我说:“感谢您的盛意,但是我还有别的片子要拍。”她说:“我可以等你。”
这一等就是两年的收录时间,直到《边走边唱》完成后我们又去了戛纳电影节参加比赛的时候她又来了,这件事就是在那个时候才确定下来。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徐枫女士是《霸王别姬》这部电影的第一位开启者,是第一位功臣。
她一直对我说在《侠女》之后她有一个愿望,她非常希望带着另外一部影片去戛纳,得到一个更大的奖。
这个金石为开的结果便是她的夙愿居然实现了,在两年以后的1993年,这部电影在戛纳获得了金棕榈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
至今我都觉得徐枫女士是独具慧眼的一位制片人。
张国荣、徐枫、陈凯歌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第二个大功臣是原小说的作者李碧华女士。
我到香港见到她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才高八斗,异想奇思,非常有创作上的活力,是很有趣的一个人。
不管是她的《胭脂扣》,还是其后拍的《青蛇》我都觉得非常好,好就好在她的故事是顺着人情走的,而不是顺着一个目的走的。
她写的东西轻轻巧巧,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包袱,不教化人,而是让你随心去品味俗世人间的故事,所以她的东西写的非常非常顺畅,我们也聊得非常好,决定一起来合作这样一部戏。
所以说起来李碧华女士其实是《霸王别姬》的母亲,她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她就是那个为影片打基础的人。
从小说到电影
其实我也听到过一些批评的声音,说《霸王别姬》说到底就是一个通俗故事。
我宁愿把这样的评价看成是一种表扬。
这让我想起沈从文先生在世的时候曾和他的同乡,写过《芙蓉镇》的古华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倘若你自己的创作太过用力,从某种角度上看太深,你就无法去表现你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也会使读者感到吃力。
这段话我读到之后对我很有启发,电影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表现普普通通的人的感情,一部电影当中的情感应当被观众接受到,故事在于怎么讲而不在于故事本身,阳光之下无新事大家应该都清楚。
我也想起唐朝诗人温庭筠的一句诗,曾让我琢磨过很长收录时间,他说“满宫明月梨花白”。
我说这个“白”字是再通俗不过的一个字了,一般难以入诗,但是它好就好在,这一个字把月光给写绝了。
所以我觉得是普通的字,普通的情感,不同的属于个人的表达方式,是一部电影非常重要的一些元素。
在这部电影里大家会看到有两位署名编剧,一位就是小说的作者李碧华女士,还有一位就是芦苇老师。
我通常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和编剧们一起工作的收录时间非常长。我通常会花少两三个月甚至五六个月、一年的收录时间和编剧进行沟通,其实就是两三个人在一起坐禅,去琢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霸王别姬》的这个过程大概是从一九九一年的六七月份从戛纳电影节回到北京之后开始的,影片本身是从一九九二年的二月中旬开拍的,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用八九个月的收录时间才完成了这个剧本。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剧本的初稿写好以后,大概是一九九一年的年底,芦苇老师给了我一支笔,说如果哪个剧哪个场次你满意,就画一个圈,结果初稿只有几场戏是画了圈的。
创作相当艰苦。
这个过程我感觉其实是挺复杂的一个过程,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面对《霸王别姬》这么一个故事结构时——
片中收录时间的延展大概有五十年左右——
我们首先想确定的就是,这个故事是跟着事件走呢,还是跟着人物的性格走。
我们大家都知道“情节是性格史”这句话,有什么样的人物性格才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决定不走事件推动情节的路子,让性格成为这个故事发展的动力,从人物的性格入手。
这里首先要确定的就是程蝶衣的性格,因为他是整个故事的种子,当然还有段小楼和菊仙,这三个人构成了非常生动的人物关系,两男一女或者,两女一男,全看你观察的角度。
故事就是围绕着这三个人展开的,而我们希望始终追随程蝶衣,因为他是影片的灵魂。
在这里想说一下程蝶衣这个人物在整个电影中的核心作用,在从原小说到电影的过程中这个人物经过了一些调整。
他的性格十分强烈,电影中很多地方也都突出了他的这种性格,这也是从文字到电影戏剧化的一种转化。
大家看完电影之后都记住了“不疯魔不成活”这句台词,电影中用了很多种方式把他的这种思想反复地强调并用电影化手段表达出来,这其中还是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程蝶衣的人物创造
程蝶衣性格是由三个条件决定的:
第一,他是妓女的儿子,从小生长在勾栏青楼之中,见惯了风月之中的肮脏,他痛恨反感这样的男女关系。
第二,他的童年少年是在戏班中度过的,那时戏班的孩子不许和外界接触,因此不谙世事,不懂世故,换言之,就是一派天真,这样的人进入社会,不死才怪。
第三,他有六根指头,这个设计原小说中没有,我提议加进去,有隐喻的含义。
第六指,即生殖器官,对程蝶衣而言,不断此指成不了旦角,也无法在心理上进入女性的世界,不断指完成不了“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转变,这一点是程蝶衣“雌雄同在”的基础。
而前面两点:
第一,他在青楼中对男女关系的痛恨,让他怀抱霸王和虞姬从一而终的梦想,可这是台上的事,理想化的;
第二,戏班中的封闭世界让他不懂得随波逐流。
这两点加起来就成了“人戏不分”,在现实生活中他始终无法从他饰演的角色中剥离出来,成为现实的,油腻的程蝶衣,而只能台上是谁,台下还是谁。
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注定了他与世俗世界的对峙状态,注定了他要饱受磨难,也注定了他将保持一直抗争不肯屈服的本色。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叫污淖陷沟渠”,我觉得这两句曹雪芹形容林黛玉的诗在程蝶衣身上得到了为充分的体现。
在整个故事过程中,他的性格在情节发展中不断发酵,从忍受断指之痛后不断遭受毒打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性别认同,到为了忠于霸王宁愿逃跑之后又回到戏班接受更为残酷的惩罚,再到为了救霸王可以为日本人唱戏然后在法庭上非常天真的说“青木不死,京剧就传到日本国去了”,不懂人事啊,只迷恋于自己的舞台。
我在《霸王别姬》拍完以后有一天就琢磨这故事到底说了什么呢,后来就觉得这是一个关于迷恋与背叛的故事。
只迷恋于自己舞台的程蝶衣对一切世间的事情无感,不然段小楼也不会对他说“你也不看看这世上的戏都唱到哪一出了”,直到他后黄钟尽毁,瓦釜齐鸣,烧了戏衣,别了舞台,把霸王留在心里头,舞台和人生的一元论在程蝶衣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了终的体现。
程蝶衣是一个极端决绝、多情、纯真无畏的人,这样的人物人间哪得几回见呐。
这样的人物跃然于银幕之上的时候,便是我们中国电影对人物刻画进步的时候。
程蝶衣所有的性格都是从上述的三个条件里面出的,所以程蝶衣的人物形象是独特的,是从俄罗斯三杰所说的“这一个”的创作方法中创作的。
以这种诉求为目的的创作是非常艰苦的,要经历无数次的肯定、否定、再肯定的一个过程,没有套路可寻,也无法归入某一类型。
今天以“快”为目的的创作者是大都不愿意采取这种方式的,而是以类型化的人物去演绎类型化的故事,这种情况是在常理之中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工业出不了这么多“这一个”,大工业需要的是标准构件。
但是在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总会在某个不可知的收录时间点,跳出一个反类型的人物或者故事让我们感到很欣喜,近我就看过。
所以和两位编剧进行了这样长收录时间的讨论之后,我们在一九九一年底九二年初才有了剧本的初稿,我刚才提到一支笔画个圈表示对哪一场满意或者不满意,这个稿本至今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李碧华在这个过程中也来北京参与了我们的讨论,有一点关于剧本结尾的处理我想补充一下。
在原小说中写程蝶衣终流落香港,改革开放后段小楼随团去香港演出,两人在浴室相遇,我想李碧华的原意是要写他们袒膊相见吧,但是我觉得不够有力量。
性格要素一定会驱使程蝶衣追随虞姬的步伐终成全自己,因此他的死是他的个性唯一合乎逻辑的结局,我认为这个戏的这个死亡在艺术上是成立的。
因此我建议改成十一年后两人重新见面,以程蝶衣的自刎结束全局,李碧华同意了。
影片拍成后她再版的小说中也采取了如此的结局处理,程蝶衣这样一个人物才真正完备了。
对两位编剧对影片做出的贡献我十分感谢。
在剧本讨论的过程中我自己也觉得其中包含了我自己某种开悟的契机,有些东西在我的脑子中和身体内部成长起来,譬如人物、情节、时代、节奏、甚至于连北京的气息和气味都在我的脑子里活了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拨云见日的过程,在剧本讨论结束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知道这个电影应该怎么拍了,可是我还没有程蝶衣呢。
我就是程蝶衣
其实我过去回忆过我第一次见到张国荣的情景,我是在剧本初稿还没有完成,只能以口头形式向他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去的香港。
徐枫女士为我安排的见面地点在香港文华东方酒店,也就是他十多年后纵身而下的这家酒店。
张国荣非常的安静斯文,我讲的很急,生怕我们会有语言障碍,因为我讲的是普通话,而他是一位说粤语的演员,我怕我讲的打动不了他。
我在其他场合讲过他抽烟,手指微微颤抖,在讲的过程中我有了一种排斥的心理,我暗问:我怎么知道他是扮演程蝶衣的合适人选?
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好演员,我的故事可是发生在国内的,而他是个香港人,他能理解这样的角色吗?
而我在这里疯狂地讲着一个可能遭到他拒绝的故事,他一直没说话,一直静静地听着,有时候看看我,有时候不看,我就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当我全部讲完之后,我突然认定他就是程蝶衣。
因为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坐在船头的,这个故事之船的船上的人,在船动起来以后的湖光山色,时时在变化,这些光影、水波都在他的脸上有所反应。
我不愿意说他是在演,他是紧追着程蝶衣,用一种非常含蓄的方法接近他,表达他,爱他。
然后他站起来和我握手说“谢谢你为我讲的故事,我就是程蝶衣”。
这是一个令人汗毛直立的瞬间,是我确定演员的漫长拍摄生涯中唯一一次。
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一个演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用心地去体会一个人物的演员,他甚至还不知道这个角色终是不是他,我挺感动,我的尴尬没了。
其后的事情大家都耳熟能详,当时还有一个演员也想演这个角色,我们的制片有所动摇,但是又被很多事情所困扰,譬如说宠物何时能进关之类的事情。
在有一次又发生了美国律师为宠物进关问题给我打电话的事的时候,我就有点不高兴了,可以说是发了脾气,其实我是真的希望这个谈判是谈不成的,我一直认为只有张国荣才能扮演这个角色。
后来我就二次去了香港,跟张国荣再见面劝说他不要因为中间出现了波折而放弃这个角色,他一口就答应了,说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我应该去北京学习,我说立即、马上,他在几天之后就来了北京。
选定张国荣的过程就是这样,可以说出现了波折,但后非常圆满。
我们的戏是从童年开始拍的,整个拍摄大概延续了六个月的收录时间,他来的时候距离他的戏开拍还有六个月收录时间,所以他大部分收录时间是用来学戏的。
非常感谢现在已经不在了的史燕生老师和张老师夫妻俩,当时他们负责国荣的京剧训练。
尤其是在少年程蝶衣逃出戏班又返回来,听关师傅讲霸王别姬的故事然后打了自己十九个耳光这场戏,张国荣来了。
这是一个很戏剧性的场景,他穿着一个军大衣,双臂抱着,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因为我知道那场戏要狠打就只能打一次,所以拍这个镜头的时候酝酿了很长的一段收录时间。
这个小演员叫尹治,其实打了自己十九个耳光之后牙床都已经出血了,可张国荣脸上纹丝不动,我一喊停他掉头就走,一秒钟都没停。
我本以为他会去安慰一下这个小演员,可是他没有。
过了几天我在游园的抄手走廊里面看到他把尹治叫过去说:“我和你拍张照片吧”,他就搂着尹治坐在坐凳上拍了一张照片。
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他是拿尹治当他的前世看的。他就是要看到他自己在少年的时候遭了什么样的罪。
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有心人,这个场景真是让我挺难忘的。
看了这个以后他大概就知道自己该怎么演了,记得第一天拍摄,他和丰毅在影楼里拍照片,他还替丰毅抚平衣服...
接着就是走到外面之后遇到学生抗日游行,学生们激情四溢的责骂了他们,而他却躲在了丰毅身后,我当时就感到说真不像是第一天拍。
这是他的第一场戏,而他已经入戏很深。
接着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他在拍戏过程中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说话。
有一次拍他在恭王府里头穿着一身洗旧了的中山服,带着一副塑料边的眼镜,提着一个人造革的皮包,穿着一双凉鞋,他这时候提出说要换一双白袜子。
穿上开机以后他要走过一个地上全是煤渣的走廊,他停住,提起他的脚抖了抖。
这个镜头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泪目了,像他扮演的程蝶衣这样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不死才怪。
人有洁癖世同嫌,全世界的人都讨厌他,但他就用这样一个动作把这个人物表现出来了。
当时我就想这么一个破旧的小院,铺满煤渣的走廊,怎么也掩不住这么一个演员的绝代风华,这个景是没得看的,但是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这个人物身上。
关于张丰毅
我还想说说张丰毅,张丰毅是一个出名的硬汉呐,他本身性格就是这样的。
他说别的戏我都行,就是哭费劲,然后到了菊仙流产要抓张国荣这场戏的时候,警察都到了门口了,我说你这时候不掉泪什么时候掉泪呢?!
他说你给我说点儿能让我掉泪的话行吗?我说行,于是把旁边的人都支开,只剩下我们俩。
当时他所站的位置就离要拍的机位一步之遥,我就说了一点儿关于我们父母的事儿,他听我说完掉头就站那儿,热泪盈眶。
还有一场打通堂的那戏,饰演关师傅的吕齐老师下手挺重的,我想着丰毅这么大腕儿,要真打恐怕不合适,还想着怎么做护具呢,丰毅就过来了。
张丰毅说:“不仅要打,而且要真打,不仅要真打,还得露肉”。
他自己往板凳上一趴,裤子一褪,连徐枫女士在旁边都看得不忍。
戏拍完十年之后,有一次丰毅见到我,就和我说《霸王别姬》里面他和程蝶衣说改天去逛逛窑子的时候,有一个搓手的动作是我告诉他的,他说有人告诉他这个动作不好,他自己也觉得有点过了。
我当时并不在意说这个动作是好还是不好,而是十年过去了,他还在琢磨着这件事儿,他还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这种人也是戏痴了。
所以可以说《霸王别姬》是张丰毅老师的代表作。
关于导演的个人情感
说到我和张丰毅说了什么呢,我是提起我们的父母来了,提起老辈儿的事儿,提起我们四十多年前的不堪。
说到丰毅父亲,丰毅掉眼泪了,其实当时就是说他们的境遇,包括我父亲的境遇。
从《霸王别姬》开始拍,我就处于一种极度的惴惴不安之中,因为我父亲是在开机前一个月确诊是肺癌。
在这紧张拍摄的六个多月的收录时间里,我一直就没有机会去看望他,都是我的制片主任白玉和我的妹妹陈凯燕去照应我的父亲的,我的内心当时是极度不安的状态。
我父亲这辈人真是经历了大沧桑,但是他也教给了我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个人的悲情情愫可能也糅杂到了这个电影中间。
我当时也想办法安慰我自己,我说“素衣莫起轻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我父亲也许到了清明的时候就能好了,就能回来了。
但终他的病还是越来越重,两年以后还是走了,所以《霸王别姬》这部电影永远和我的亲情融合在了一起。
我到戛纳得奖之后拿着奖杯回到家,那个时候距离他离开其实只有几个月的收录时间,他说我拿着拍张照,拍的时候那笑容真像个小孩儿。
我也有机会通过拍摄《霸王别姬》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城内四处乱走,王府、故宫、公园、道观、寺庙,各种各样的地方,其实也有一种很深的感叹在,就是这个老北京已经消失了。
而《霸王别姬》这样的故事,《霸王别姬》中间的人物都是依附于这座城市的,当这座城市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样的人就再也不会出现了,这是很强烈的一种感觉。
我在电影停机不久,杀青宴吃过,虞姬自刎之后堕入梦乡,突然就梦见张国荣穿着一身雪白的长衫,走进来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从此告别了”。
我就醒了,不知何故就掉眼泪,后来泪眼朦胧之际回想,此时距离他离世还有十年,但似乎这个梦就预示了他后的结局。
我总觉得张国荣这个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程蝶衣,扮演程蝶衣就是他的宿命,他到底还是用人戏不分,自行了断的方式为程蝶衣画上了句号。
每次想到这个地方我都强烈的感觉到命运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到底《霸王别姬》不是关于社会的,不是关于时代的,也不是关于集体的,而是关于一个人的。
从我自己的体会讲,艺术永远是关于个人。
《霸王别姬》之后
有一位已经不在的作家汪曾祺,他爸爸是画画的,他自己是写小说的,他说他从他爸爸那儿就学到了一个东西,我看之后觉得挺棒的。
他说他爸爸画画之前站在桌子前面半天,说先有一团情致出来,然后再说怎么样落笔,怎么样构思。
其实无论《霸王别姬》也好还是《黄土地》也好,都是先有了这团情致才有的,可你说这情致是什么,很难说的清楚。
我这人大的缺点就是不会算,我自己就觉得既然想做电影导演了,跟着自己的念头做就好。
所以我才会特别想到电影节这件事儿,大家都知道1993年这部片子拿到了戛纳的奖,然后到次年又拿了奥斯卡的两个提名,后来又得了金球奖等等,应该说这个电影给了我很多。
戛纳这样的电影节之所以充满了魅力,成为很多不同年龄段的电影人们所向往的电影殿堂,就因为它的不可知——
你不知道哪部电影会成功,会获奖,你也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新潮流会以什么样的新的方式突然跳出来。
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瞬间,就是1995年北欧有一个叫“道格玛”的电影流派出现了,我看了三四部他们拍的电影,真的觉得它确实是在改变着电影的方向的。
有时候你可能失败了,但是你仍然想往前走,我们知道戛纳它不仅仅是一个电影的应许之地,更是代表着年轻和希望的励志之地。
一个电影节,一个奖项如果总是老导演包揽是不对的。
我曾经在得知某个年轻导演为了自己的电影自杀身亡的消息的时候,难过得不得了。
我曾向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建议:中国导演协会的目光应当放到那些为电影而欢欣、而迷茫、而痛苦、而舍弃一切的年轻人身上,正视那些为自己的朦胧梦想,微弱的生命而决绝远去的年轻人,正视那些因失败被人耻笑而不肯低头的年轻人,让他们站到中国导演协会的领奖台上去吧!
我希望这样的事情在日后能成为中国电影的新常态。
谢谢各位。
陈凯歌在北京电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