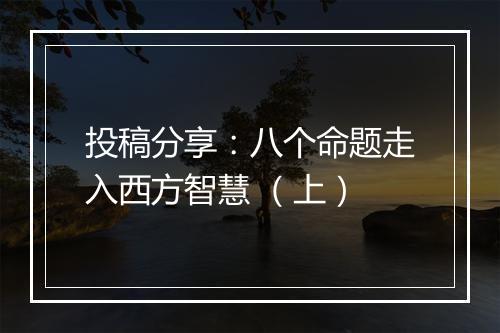投稿分享:八个命题走入西方智慧 (上)
一、认识你自己
这个命题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提出来的,确切地说,这本是德尔菲神庙门楣上的一句铭言,只是苏格拉底把它发扬光大了。《论语》中也有类似的话:“吾日三省吾身。”西方的“认识”,中国的“反省”,指向的都是人自己,但是内容却大不相同,这正反映出东西方思维和文化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的是伦理道德、立身处世和人格修为,故“三省”的内容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与此相反,苏格拉底的思想没有那么世俗化,而是立足于对真理的追求并充满了思辨色彩。在苏格拉底之前,哲学家们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世界的本原”,也就是构成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元素。古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另外一个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他曾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名言,又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还有的哲学家说世界的本原是看不到的某种“原子”,乃至抽象的“数”。这是西方哲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叫做“自然哲学”时期。苏格拉底改变了哲学追问的方向,他认为探讨世界由什么构成没有意义,这个问题恐怕永远也说不清楚,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力量使世界变成这个样子?在他看来,那就是“善”。既然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人身上也必然会体现出“善”,这就是心灵的德性。由此,西方哲学就发生了由外而内、由自然而内心的转折。
认识你自己,也就是认识自己与生俱来的德性。在苏格拉底看来,每个人都先天地拥有诸如正义、勇敢之类的美好品质,这是神平均分配给大家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世间又有好人、恶人之分呢?这是因为光有勇敢的品质还不行,还需要有关于它的知识,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勇敢才是有益的。否则,勇敢就蜕变为了鲁莽、凶狠等。换句话说,没有人想去作恶、想去做坏人,如果他做出了一些坏事,只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作恶,他在这件事上缺乏正确的知识。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又一句名言了:“德性即知识,无知即罪恶。”
进一步来说,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获取关于德性的知识。回头再比较一下:中国人关注的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做得怎么样,有否愧对自己的“先祖”、自己的“良心”;西方人关注的则是某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所谓仁义礼智信,在中国是行为的准则和道德的追求,放到西方,大概首先要考证一番它们的定义了。中国讲伦理道德,西方讲真理思辨,都是智慧,一种是实践智慧,一种是理性智慧。可以说,在文化的源头上,中西方就岔开了两条路。
二、洞穴中的囚徒
这是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的一个著名比喻,他将人比喻为“洞穴中的囚徒”。这个洞穴有一条通道通向外面,各种东西的阴影就投射在洞穴的后壁上,而人从小就生活在里面,手脚被束缚,不能动,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那么,这个人一定会认为,洞壁上的阴影是真实的。倘若有一天他被释放出来,看到了洞穴的真实情况,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那么他是无法一下子接受的。而一旦他明白了这一切,又断然不会再想去做囚徒了。
柏拉图认为,我们现在就是“洞穴中的囚徒”,我们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都是假象,都是虚幻不真的。真实的世界在哪儿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画一张桌子,其实是摹仿现实中的桌子,而现实中的这张桌子又是摹仿了“理念世界”中的桌子。作为图画的桌子只是个仿品,现实世界中的桌子也是仿品,只有理念中的桌子才最真实。这种思维对于中国人来说,恐怕会有些难以接受,硬说看见的是假的,看不见的、只能用理智去领会的才是真的。其实,这正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总要为世界找到一个基础,总要去认清现象背后的本质,总要为事物的存在和秩序找到一个根由。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两个词是“仁”和“道”,“仁”并不玄奥,说到底就是基于血缘亲情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情感;“道”有一点接近西方,是对世界本质的界定,但老子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把它打发了,那是不可说、不可思的东西,《道德经》反复说的还是“大智若愚”“上善若水”之类与世俗生活相关的人生智慧。但在柏拉图眼中,现实世界中的万物变动不居、生生死死,令人不可捉摸,一定还有一个永恒完美、秩序井然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各种理念构成,最高的理念就是“至善”,万物摹仿它们而存在。你怎样去反驳他呢?很困难。柏拉图会说:“可怜的囚徒啊,你被困于洞穴中,哪里知道世界的真相。”不过,有些时候我们对于这个理念世界也会心有灵犀,比如“柏拉图之恋”:任何现实的爱情总是有瑕疵的,唯有理念中的爱情,永远被向往和追求而不去落实的爱情,才是最完美的。
三、我思故我在
“我×故我在”这个句式,近些年来很流行,比如“我唱故我在”“我舞故我在”“我爱故我在”等等。这话原本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年)说的,作为哲学家的笛卡尔我们也许比较陌生,但他还是一位数学家,坐标系和解析几何就是他发明的。在古希腊哲学之后,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以神学为中心的中世纪时期,随后是文艺复兴,然后就到了培根、笛卡尔们的时代。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培根我们都知道,他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这是一个崇尚科学知识的时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
这么多知识,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为什么正确又为什么错误呢?科学体系又是怎样一步步地建立起来的呢?笛卡尔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找到一个确定无疑的基石,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怀疑而永远正确的基石。有了这个坚固的起点,然后运用演绎推理,由简单到复杂,就可以推演出一整套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
笛卡尔采用的方法是“普遍怀疑”,也就是说,先把能怀疑的全部排除出去,看看是否能留下什么无法怀疑的东西。于是,天是蓝的,云是白的,地球是圆的,石头是硬的,此类都被排除掉,就连“我”的手和脚甚至整个身体也可以排除掉,最后,上帝也不能幸免。剩下来什么东西呢?唯有一件事情无法怀疑和排除,那就是“我在怀疑”或者说“我在思想”这件事。“我”怀疑“我在怀疑”,这就等于说满头白色的黑发,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我在怀疑(思想)”是一个没法被怀疑的基石,问题就好办多了,总有一个东西在怀疑吧,那就是“我”,因此,我是存在的。于是乎,笛卡尔的命题就出现了:我思故我在。
当然,这个“我”是精神性的,是具有反思能力的;最关键的是,对自我的确认成为关于这个世界所有认识的基础。什么意思呢?人的力量被彻底解放,人的思维、知识被推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成了世界的“老大”,也就是所谓“高扬人的主体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少有这种想法,我们有的是“道法自然”“敬天法祖”,有的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思故我在,我在故世界在,对中国人来说,这些不算“狂妄”的话,也是莫名其妙、云山雾罩的念头,想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当然,这还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四、哥白尼式革命
“哥白尼式革命”说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年)的哲学创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哥白尼和康德这两个人。在很早之前,人们以为太阳绕着地球转,哥白尼却说:“你们错了,应该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现在幼儿园的小孩子都知道的事。再说康德,无论怎样强调他在西方哲学和文化中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海涅评价道:“康德这人的表面生活和他那种破坏性、震撼世界的思想是多么惊人的对比!”康德一生未婚,终日沉浸于哲思,每天按时散步,据说邻居看他出门的时间都能对表。就是这样一位哲人,在西方哲学史中掀起了一场划时代的“哥白尼式革命”。简单地说,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桌子是方的在前,我们就如镜子般反映出、感受到桌子的方。康德将它反了过来:桌子本身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桌子之所以是方的,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方的,而是因为我们用“方”这种认识形式去感受它。哥白尼把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反过来,康德把对象和认识的关系反过来,此谓“哥白尼式革命”。
这想法与笛卡尔一脉相承。笛卡尔的意思是:我存在,世界才存在。康德的意思是:我用这样的方式去认识世界,世界才呈现出现在这个样子。接受了唯物主义教育的我们,恐怕很难接受这些看法,甚至会觉得荒诞不经。不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物质吗?切莫急于下论断,康德同样会认为我们的想法幼稚,不妨听听他怎么说。
康德是要解决“知识的可能性”问题,也就是问:我们的知识是怎么构成的,处处适用的知识怎么就有了普遍性?最简单的:为什么这张桌子谁看都是方的?我们会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就是这样嘛,天生如此嘛。这样一说就漏了陷,我们没有康德富有批判精神,怎么就“天生如此”了呢,连这都说不清楚还谈什么知识?在康德看来,我们之所以能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先天的认识形式,就好比某种月饼看上去同一个样子,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模子制作出来的。再好比说,水本没有形状,盛在圆的容器里它就是圆的,盛在方的容器里它就是方的。世界本来也没有什么它自己的形状、大小等等,我们用“方”“圆”去观察它、认识它,桌子才是方的,西瓜才是圆的。到了康德这里,西方哲学有了一次飞跃,要想认识世界,必须先考察一番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也就是要解决我们具备什么样的认识能力、知识怎样构成等问题。眼睛正常的人和色盲、近视眼,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但看到的景象却并不相同,不正是因为他们的认识能力不同吗?倘若每个人都是色盲,那么,我们会怀疑自己的眼睛有问题吗?显然不会,我们只能猜想,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那么,我们有哪些认识世界的“先天形式”呢?这就进入康德庞大的思想体系了,我们之前只是在努力走到康德的家门口。康德说这些先天形式有三个层面,感性、知性和理性,为此他写了三部著作,即“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适时打住吧,要想读透这三本书,我们可能要付出一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