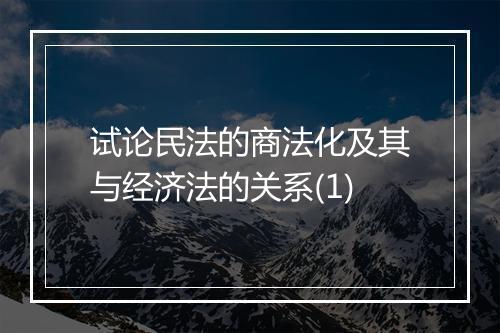试论民法的商法化及其与经济法的关系(1)
本文从商法、民法与经济法各自的产生、发展出发,探讨现代社会中民法的商法化和社会本位化,将其与经济法作一比较,试图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调整模式的基本构成。 法律部门的划分,主要是“属于法学范畴的学理探讨,它与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需由立法者(暨立法)和法学家的主观意志作为中间媒介”。
由此出发,法律部门的划分,法律调整模式的设计,应当不仅仅强调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还应当渗透着法学家的主观意志。从根本上说,某一法律部门成立与否,是由相应法律规范的特性及其立法宗旨和占主流的法学学说所决定的,法律调整模式的设计应当立足于一国的法制实践。
一、商法的产生和发展 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它起源于
1
1、12世纪的西欧国家。当时城市规模扩大,导致了职业商人阶级的产生。
“正是主要为了满足新的商人阶级的需要,才形成了一种新的商法体系”。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城市的发达与自治又促使商业联盟、商事习惯和商事法院得以发展。
从中世纪到近代,调整商事行为的制度和法律规范不断出现,并在体系上逐渐得到充实,从而确立起商事管理、商事票据、商事公司以及银行和商业信用等制度。至16—17世纪,为了谋求国家的富强,政府加强对商人阶级的控制,各国均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将商事习惯上升为法律,后又相继出现了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17年的《卢森堡商法典》、1829年的《西班牙商法典》、1888年的《葡萄牙商法典》、1838年《希腊商法典》、1838年的《荷兰商法典》、1850年的《比利时商法典》、1865年和1883年的《意大利商法典》、1900年的《德国商法典》等。
欧洲大陆的商事立法热潮,是商人利益的典型体现,也是立法者秉承商人习惯法这一成型规则的传统做法。因此,商法从一开始便带有商人习惯法的局限性,是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的产物,其制法过程缺乏类似于民事立法那样的理论准备。
在缺乏理论准备下建立起来的欧洲各国商法体系,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其内容不断修改和补充,成为发展和变化迅速、但又缺乏理论指导的法律部门。 19世纪以来,商法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加之上述原因,从瑞士民法典开始,出现了民商合一的趋势,调整商事关系的商法典模式逐渐由民法加上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单行法规调整的模式所取代。
这些根本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的商化和商化的人。经济和经济民主的发展,导致人的普遍商化,使商法规定的商人很难与自然人和法人相区别。
法国商法和德国商法分别采用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试图将商事法律规范与民事规范区别开来,但是这种努力显得越来越勉强,从而损及商法得以独立存在的基础。 2.商事行为的泛化。
不仅仅是商事主体出现了普遍化,商事行为与其他民事行为也难以区分,“营利性”标准随着现代经济生活对效益的追求已经不可能使商事行为独立。同时,商事行为的范围越来越大,商法对于经济生活的保障显得力不从心。
3.国家职能和角色的转变。现代国家集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和经济参与者三位于一体,对于经济生活越来越需要统一的调控、管理和参与,缺乏系统理论和统一性的商法难以胜任这种需要,这是现代商法渐次式微的根本所在。
而且,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商法本身理论的先天不足也使其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首先,商法的调整对象“本质上是某种生产经营关系,此种社会关系是由营业性主体所从事的营业性行为所形成的,其范围包括了一定社会中生产交换和分配各阶段上形成的基础关系”。
由此可见,商法独立的基础在于其主体制度及与之相联系的商事行为,而事实上,商人特殊身份的消失和商业的泛化,使商法独立于民法的依据已不复存在。 其次,商法本身的体系纷纭芜杂,难以形成共同的法律原则,“组成它的几个法律相互之间,并没有完整的内在联系”。
各国有民商合
一、有民无商、有商无民、无民无商等各种模式。法国商法采取行为主义即客观主义,包括通则、海商、破产、商事法院各编;而德国商法采取属人主义,即主观主义,包括商业性质、公司及隐名合伙、商事行为、票据、海商诸编;日本商法则有总则、公司、商事行为、票据、海商等编。
这些法典的范围不尽相同,各国又对之作重大修改,相应颁布了多种单行法规,“可知商法应规定之事项,原无一定范围,而划分独立之法典,亦只自取烦忧……关于商法则不能以总则贯全体”。 最后商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逐步公法化的特征。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民法所调整的常常是个人的福利,保护的是公民个人的利益关系,而商法所调整的内容常涉及公共福利,更多地保护着公共利益关系”。这种观点并未真正认识到现代民法发展的精髓。
尽管商法中有众多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规范,但它仅仅表现为国家对商事行为的形式性要求,它和民法意思自 治的客观化、表现化是一致的。传统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过渡,事实上就是民法逐渐向商法靠扰的过程,商法学者提出的商事公法、商事私法的理论本身,就反映了他们既希冀利用传统法律部门来解释现代国家参与调控经济的现实,又企图维持自由竞争时期发展而来的私法自治的矛盾心理。
商事法律规范本身缺乏共同性,“民法和商法的分立并不是出于科学的构造,而只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商法并不超越民法的范畴,二者都必须贯彻私法自治或当事人自治的原则”。
可以说,商法的产生和发展表明,它在实质上是为了弥补系统的民法未及问世之需,在国家与私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应急物。对于我国而言,既缺乏商事惯例传统,也不存在商人集团这一现实,更不具备理论准备,因此不存在使商法独立的事实根据和逻辑上的必要性、充分性,民商合一才是中国法制的必然选择。
二、晚近民法的社会本位化和商法化 民法作为传统的法律部门,从罗马法以来一直以自由的契约法为核心,“它以民事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制度为核心,主要调整当事人意思自治,亦即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财产流转关系,并建立相应的主体制度、物权和其他权利制度,与刑法衔接调整较轻微的侵权关系”。[12]民法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现代民法不再采取权利本位(权利本位的真正含义就是个人权利本位),[13]而是以公共利益、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等原则约束的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的。
个人主义的勃兴形成了传统民法的精髓,即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私法原则。而在现代社会中,“为了减缓自由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以期合理配置资源,资本主义国家则由治安警察国家过渡到行政国家,主动介入‘市°民社会’的‘私生活’”,[14]因此,从法国民法典的传统民法,发展到1919年魏玛宪法所规定的“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当同时符合公共福利”,以及日本ง战后增补民法第1条关于“私权应服从公共福利”的规定,民法已从权利本位发展到社会本位。
今天,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都已实现了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应运而生。[15]在罗马法中,“人的活动是自由的,国家保护它不受侵犯……法律保障给予某一主体以求生存和幸福的资料总和是他的财产,因而这种权利本身被称为财产权”。
[16]物权体现人对物的权利,债权体现的人对人的权利,这种完整的权利世界观是围绕着财产构成的。与此同时,人格独立、自由、尊严等通过意思自治和民事法律行为来完成,传统民法的契约自由典型地表现出这一特点。
“契约自由被视为意思自治的核心,它使当事人有权摆脱法律为他们提供的一切固定模式而自由地设置其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17]因此,传统民法的精髓在于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财产的稳定性(物权制度)和流动性(债权制度),从人的自由与对财产的完整性保护这两个基点,完成了传统民法理论大厦的构筑。
社会本位的民法对所有权加以限制,促使所有权社会化,出现了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和消费者、公平竞争、解释契约的表示主义条款、限制利息租金和价格、禁止房屋出租人强制承租人搬迁、限制权利的履行、限制卡特尔和不当赠与契约、禁止不当招徕等等,所有这些,表明了国家对私权的限制。传统民法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它是同民法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变化紧密相关的。
这些变化表现在: 1.债权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市民生活和经济活动的范围扩大,人与人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为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
由此出现了保护交易安全、防止权利滥用,债权逐步优先于物权的趋势。人更注重物的价值而不是物本身,财产组成的债权化,人与特定物的联系弱化,这使法律更加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人与人的合作。
2.意思自治受到限制。这是现代民法最重要的发展。
合同的特殊意志随着社会精神约束力的削弱,越来越侵蚀国家与社会的利益。“法以普遍意志的面目出现,在保障自由意志的同时,逐渐对特殊意志的自由度施加拘束”。
[18]社会现实越来越需要外在性的约束控制机制,合同内在的形式与实质的矛盾,形成了合同法律制度中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冲突。意思自治的衰落与现代民法的发展是一致的,它表现在:强制性合同大量出现;合同中的意思主义逐渐为表示主义代替;合同解释由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趋向于使之产生法官所希望的法律效果,即根据“当事人的意愿要订立公平和符合社会利益的合同”[19]来进行解释。
民法中意思表示客观化和形式主义的发展使其得以与商法相融合,对民事法律行为严格要求正是其“公法性”的体现,国家通过对特定商事行为形式的要求实现商法的特殊调整。许多学者仅仅强调商法的公法性,却未看到这种公法性是建立在强调自由意志基础上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现代民法中强行性规范的增加,正是其社会本位所在。 但是民法的本质在于个人意志 的自由,任意性规范才是其精髓所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并不改变民法的性质,而只是缩小自由意志的范围,导致民法生存的危机。
“现代民法中法律行为的效力与法律规则效力之间的矛盾显然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法律行为调整方式与法定调整方式之间的矛盾显然也不可能得到适当的协调”。[20]因而,社会生活的发展使得民法的意思表示越来越外在化,越来越趋同于商法,民商合一的趋势使得现代民法出现了无法解决的二难选择,意思自治与实现有效社会控制这一对矛盾无法在“民法—商法”的架构下得到调和。
在商法无法适应现代国家职能转变的要求时,为了保持民法的自治性,实现经济法与民法的接轨是现代法律体系的必然选择。
三、经济法: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毋庸质疑,商法的公法化为许多学者解决民法遇到的危机提供了一种思路。 “在商法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里,新的经济法仍然在为自己谋求一席之地,一般来说,它仍然难以有足够的力量来充实商法”。
[21]事实上,尽管经济法与商法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国家干预的因素,但商法仅仅是通过对意思自治形式化的要求,实现对商事活动的调整,它仍然是由“私的”法律规范组成的。例如商事公司法,它仅仅是从资本组成、成立程序等方面对经济关系作外在的规定。
经济法则不同,它从组织、内部结构、管理、财务、资本运动等方面,深入经济关系内部,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因而正如学者所称,“在☼公有制企业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传统商法的内容基本上都可归入经济法”。[22] 经济法的出现与特点,是由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所决定的。
现代国家中组织的日益扩大,即所谓的“横向一体化”与“纵向一体化”。“企业是许多专业化的个人组成的集合,处于相继生产阶段领域或相继产业的专业化的企业之间的合并被称为一体化,这一概念是与专业化相反的对应”,[23]而组织是靠纵向的行政权力指导分配资源的。
[24]推动社会变迁的因素不仅仅是技术,制度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25]制度的变化是国家、组织(企业)与个人之间进行社会博奕的结果。
组织的不断扩大是传统市民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最大不同。传统法律以国家与个人为基点构筑体系,但是垄断、跨国公司、国家参与生产经营和市场操作的发展,使得以财产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以个人为基本主体的民商法无法深入组织内部和(国有、公有)财产权内部进行调整,这种调整的任务不得不由经济法来承担。
现代国家职能的转变也是经济法兴起的重要因素。为了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国家在各个方面——包括经济生活、社会保障、国土开发和人口等方面进行调控和管制。
“20世纪以来,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不介入经济生活的旧体制,越来越加强干预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26]国家在经济领域内,作为再分配人通过财政、货币、就业、产业等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所有权人通过参与经营、对企业组织的钳制,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维持人通过反垄断、保护公平竞争等经济政策,实现了对经济的完整参与、管理,通过公共供给政策、公共引导政☠策和公共规制政策[27],实现对经济调控的目标。
国家职能的发展和国家作为不同主体的角色的分离,是现代经济生活发展中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28] 社会关系的变化体现在法律上,是“组织因素”、“权力因素”法律规范的增加。
正如美国学者加贝尔指出的:“最正确地表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调整原则已经不是自由竞争,而是稳固的合作,在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工业中资本日益垄断化,劳工在工会中越来越集中,随着国家进入市场,公共企业的出现,确保失业者购买力的金钱的再分配——所有这些过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向所谓的多元主义社会经济的过渡……多元主义需要的法律模式是政府官员的调整干预,是当事人之间的合作或道德行为”。[29] 传统民商法Ⓐ是以财产关系为调整对象,在其哲学观中,财产被视为自由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由此出发,在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其社会本位只能是外在的、国家对个人意思的硬性规定,从而难以适应现代经济所要求的合作主义。经济法则以组织管理关系为调整对象,以实现国家的宏微观调控为目标,“这种由组织为基本主体参加的,由管理因素和财产因素相结合而构成的经济关系,也应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律调整的主要方向和重点”。
[30]组织因素的法律规范的增加,体现在法律领域的多个方面。在物权领域,国家所有权的经济化和广泛发展,使国家从多方面来实现其所有权,包括国有企业运营中的组织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形成。
“对此,民法中的源于罗马法的典型的私人所有权制度,即关于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抽象规定,是无法实行有效调整的”。[31]在债权领域,则出现了政府经济合同,“当我们论述现代契约关系时,有必要加上一个新的因素——权力、等级和命令,虽然权力、等级和命令在原始契约关系中决非不存在”。
[32]合同的异化突破了 经典合同法的纯粹财产关系的范畴,合同已不单纯是民法债权的内容。 显然,组织因素的增加,使得调整各别主体意思自治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已很难再象以往那样对经济进行系统而有效地调整。
尽管民法商法化、“私法公法化”的趋势使许多学者试图以商法代替经济法,希望以现代民法的社会本位来代替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和参与。但所谓民法的社会本位,仅仅是对意思表示的外部限制,外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以及形式主义的发展;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却是立足于组织和国家的新发展,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的内在协调,这是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更为深刻的内容。
“概括地说,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法就其性质来说除了不能调整组织管理性质的所谓‘纵向’经济关系外,还有一些‘平等主体’间的所谓‘横向’经济关系或契约性关系,也因为加进了组织管理因素而超出了民商法调整的范畴。”[33]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民法需要经济法来对组织关系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和参与加以调整,以保持其意思自治的纯洁性;经济法也需要民法来对市场经济的基础关系加以调整。经济法不可能将民法排斥在经济生活以外,它与民法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保证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益的实现。
“民法中的公共道德或公序良俗条款,可以说是民法与经济法的一个‘衔接点’,被认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条款的行为,即超出民法调整的范畴,而须由经济法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作具体调整”。[34]经济法的责权利效原则真正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正如美国学者所称的,现代市场经济是责任市场,[35]它通过专业化、技术化、社会本位化的法律规范来保护社会整体和个体的利益。
总而言之,经济法实现了对现代经济的高层次的调整。 当前,一些人对经济法抱有不恰当的理解,认为经济法就是国家干预法。
而事实上,经济法的根本任务是保证经济民主与促进竞争,其精髓在于对国家管理和参与经济的有序化控制,规范政府经济行为,防止其滥用职权。经济法的哲学观是统分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通过对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协调而实现与民法相同的价值目标。
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公有制占有主导地位,必须将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因为“社会主义是天然的,以社会为本位的制度”。[36]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经济法与民法应当携手并进,经济法通过它的国家所有权、经济责任制、经济合同、[37]经济管理、竞争与消费者保护等各项制度,与民法中的物权、债权和民事主体制度相衔接,共同实现国家的立法目标。
“公有社会的理想应当这样界定和实现,以便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个人自治的意义以及使个人自治与权威彼此相容”。[38]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模式的建立,应当立足于我国公有制的现实与传统,以民法为基础法,以经济法为基本法,两者均以社会为本位。
如果试图完全以民法来对市场关系加以调整,必将陷入要么不顾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坚持私法自治,从而去“补资本主义课”的道路;要么为了顾及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而使行政和民事的强行性规范压过民法固有的任意性规范,抹煞民法的精髓,不顾我国是一个个体利益发展不充分,急切需要发展私法的国情这一泥潭。 注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史际春:《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批判》,《当代法学》1992年第
3、4期连载。 参见董安生等:《中国商法总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美]H.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参见前引董安生,第14页。
参见前引董安生,第33页。 刘文华:《当前经济法学理论研究中应关注的几个问题》,天津高等工科院校经济法研究会年会论文。
史尚宽:《民法总论》,台北1980年版,第51页。 范键:《德国商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粱彗星、王利明:《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 史际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经济法》,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12] 前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经济法》。 [13] 参见前引史尚宽,第30—32页;史际春:《从民法看法本位》,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7期。
[14] 前引《从民法看法本位》。 [15] 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16] [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3—94页。 [17] Carbonnier,Les Obligations,P.46,转引自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第15页。
[18] 史际春、邓峰:《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关于经济合同重新定位问题》,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1996年年会暨武汉学术讨论会论文。 [19] [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6页。
[20]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21] [美]丹尼斯·特伦:《商法与经济法》,载《法学译丛》,1986年第4期。
[22] 史际春、徐孟洲:《大陆六法精要·经济法》,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4页。 [23] 马九杰、邓峰:《企业制度改革方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24] 参见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25] 参见L·E·戴维斯、D·G·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概念与原因》,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6] 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基础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页。 [27] 参见[日]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页。
[28] 参见前引马九杰、邓峰,第134—137页。 [29] 转引自朱景文:《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
[30] 前引潘静成、刘文华,第39—40页。 [31] 前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经济法》。
[32] [美]I·R·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33] 前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经济法》。
[34] 前引《大陆六法精要·经济法》,第14页。 [35] 参见前引麦克尼尔,第31页。
[36] 前引徐国栋,第93—94页。 [37] 关于经济合同的定义问题,参见前引《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关于经济合同重新定位问题》。
[38] 转引自[美]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