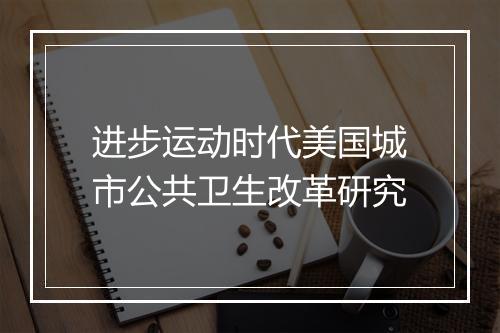进步运动时代美国城市公共卫生改革研究
摘 要:街道卫生是城市行政运行系统中的重要内容。19世纪美国城市化加速发展,首位性城市纽约居民健康严重恶化。70年代以瘴气致病论为理论基础,纽约市在全国率先开展街道卫生改革,由此掀开了美国城市公共卫生改革的序幕。90年代借进步运动东风,乔治・韦林将这场街道卫生改革推向高潮,城市街道焕然一新。纽约市也为美国其他城市环境治理树立典范。
关键词:纽约;街道卫生;改革
作者简介:李晶,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从事美国城市史和美国医疗社会史研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SWU150944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SWU1109041
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1-0164-09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是美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当美国社会正沉浸在由农业国向工业国,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巨大转变所带来的无限荣耀时,资本主义重个人、轻社会、推崇自由放任理念的弊端暴露殆尽,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一股针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的浪潮也正浮现于美国社会,史称“进步运动”。在这场纷繁复杂的改革运动中,有一场萌发于城市社会,关乎民众生命安危和生活品质的“公共卫生改革”极富个性。其中,纽约市1既是进步时代最早开展公共卫生改革的美国城市,同时还引领着整场改革的节奏和脉络,充当着各项具体改革措施的“试验场”。纽约开展的街道卫生改革,是公共卫生运动初期,美国政府以瘴气致病理论为指导,围绕城市环境展开治理的典范。经过这项改革,极大地改变了纽约街道的污浊面貌,带动了其他城市环境卫生治理工作的展开,许多治理思想和方法甚至对今天大城市环境治理仍具现实意义。
进步时代的改革运动一直是国内外美国史学者热衷的叙事对象。目前,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层面,基于公益的社会管制研究相对缺乏。公共卫生作为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开展社会管制的重要内容,在国内研究寥寥,专门针对城市政府在这一领域的管制研究更不多见。1从公共卫生视角,考察城市街道卫生改革亦存在不足。2在美国学界,研究美国城市公共卫生政策的综合性成果虽不少见,但对进步时代纽约等城市街道卫生改革的研究只略有涉及,且较为分散,针对纽约街道卫生改革与进步时代美国城市公共卫生改革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研究,部分学者甚至忽略了街道卫生改革致力于改善城市居民健康的初衷,而过分强调其在环境美化方面的意义。3本文主要从公共卫生的视角,考察进步时代纽约开展街道卫生改革的原因、内容及影响,厘清这场街道卫生改革在美国城市公共卫生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19世纪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触发了美国城市化的闸门,其中东北部城市纽约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1820年纽约市凭借12.37万人口超过费城,成为全国最大城市。仅仅30年后,纽约人口超过50万,成为西半球最大城市。[1](P16,33)这样,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纽约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工业革命后聚集经济产生的规模效应,迅速发展为全国经济的中心,各国移民心目中的财富天堂,确立了直到今天都未曾被撼动的全国首位性城市地位。然而,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却以大肆破坏生活环境为代价。纽约市作为当时全国发展速度最快,城市规模最大的城市,自然与其他城市相比,更早面临严重的城市环境问题。其中,街道卫生状况的恶化最为突出,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格外明显。
19世纪初纽约市依然延续着自殖民地时期形成的街道清扫办法,垃圾清扫被看作居民的个人事务。虽然市政府多次颁布法律,强调居民个人负有清扫房前屋后垃圾的责任,但是从政府到居民,在淡薄的卫生意识下,仅仅强调城市美观很难让这些法律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同时,大量涌来的外国移民无疑让纽约原本凸显的街道卫生问题雪上加霜。从1840年至1860年间有近180万爱尔兰人来到北美,其中大部分是经由纽约进入美国的。[2](P155)这些移民在构成上多数为贫穷农民,在生活习惯上保留了众多落后的农村卫生习惯。19世纪70年代垃圾收集工人在夏季曼哈顿的街道,每天大约要收集1100吨垃圾,而那些远离主干道的街巷,由于缺乏管理,垃圾如山更是司空见惯。[3](P14)于是,垃圾满街、污水四溢、腥臭难闻,成为纽约城市街头的常态。
纽约街道不堪入目的另一原因是当时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有轨马车。19世纪50年代,有轨马车凭借速度快、载客多以及运营成本低等优点,很快赢得了美国城市交通运输系统的青睐。然而有轨马车在城市中的广泛应用,却给城市环境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恶果。城市中日渐增多的马匹,成为街道垃圾的主要生产者。19世纪末纽约市的马匹数量达到13万匹。数目惊人的马匹每天制造出大量的粪秽垃圾。可是城市中低效的垃圾处理系统根本无法对这些粪秽作出及时处理。“据估算,一只健壮马匹每天排出的粪便在15至35磅间,排尿量达一夸脱,而这些粪秽大多被直接排泄在街道上。布鲁克林每天产生的马粪重达200吨。”[4](P20)不仅如此,19世纪80年代,每年死于纽约街头的马匹数量就达1.5万。[5](P69)这些马匹尸体要么堆积街头,长期无法处理,要么被丢入水沟,任其腐败,散发恶臭,蚊蝇铺天盖地,漫天飞舞。工业文明突飞猛进的美国城市,竟有如此恶劣的街道卫生,着实让人咂舌惊愕。
最后,面对城市规模的急遽发展,纽约市政管理的€缺失和腐败也助长了街道卫生环境的恶化。如果说在工业革命以前,纽约有限的人口规模,还能使荷兰人统治时期延续下来的街道卫生条例发挥一定效用,那么随着工业革命深入,城市化进程加快,纽约滞后的街道卫生管理体系早已不堪重负。1807年纽约市政府开始将垃圾收集工作承包给一些私人公司,但是这种街道清洁系统存在很大弊端。[6](P181-183)由于私人清扫公司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收集街道上的有机粪便,然后将其出售给耕地农民。这样私人公司在垃圾收集过程中,往往对收集对象具有明显的选择性,那些无法作为肥料的垃圾经常被弃之街头。与此同时,私人公司为了从市政府获取街道清扫合同,经常贿赂市政官员。而市政官员为了从私人公司谋取巨额回扣,又大幅提高街道清洁服务的价格,使得街道清扫成为市政服务中的肥缺,最终为市政腐败埋下隐患。[7](P183)此外,杰克逊时期所倡导的“小政府”理念,也限制了城市政府在街道卫生管理方面大有作为。 于是,进步时代以前的纽约市政府在街道清扫方面更多承担的是监督之责,仅当疫情临近或者城市垃圾问题特别严重的时候,才被迫采取直接干预的临时举措,而且从各种措施的实施力度和效果来看,社会各界对城市环境的重视程度也还有待加强。那时,各种致病理论争论不休,城市疾病预防尚缺明确的指导思想。城市公共卫生的改革者们意识到,要唤醒社会各界对街道卫生的真正重视,还要将街道卫生与居民健康联系在一起。
19世纪美国医学界关于疾病的起因与传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疾病产生于患者与健康人群的直接接触;另一种认为疾病是由于动植物腐败所产生的有毒气体(瘴气)被人体吸入后产生的。与这两种病理观相对应,医学界内部形成了相信疾病可以通过人际传播的“感染派”和认为疾病源自所处环境,不会人际传染的“反感染派”。[8](P32-33)长期以来,由于天花等通过飞沫方式直接传播的恶性传染病,给人最直观的经验便是疾病具有接触传播的可能。因而历史上,通过检疫防止患病者与健康人群直接接触成为疾病预防的主要手段。换言之,“感染派”一度在疾病预防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19世纪黄热病、霍乱等借助蚊子和水体媒介流行的传染病开始在美国肆虐,人们发现与患者直接接触也未必出现疾病症状;另外,“检疫措施”影响正常商业贸易,同时还限制个人行动自由,这与社会盛行的个人主义和重商主义也发生抵牾;加之英国查德维克在“瘴气致病论”指导下在伦敦开展公共卫生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就,都使美国主张通过环境治理预防疾病的“反感染派”势力开始不断增强。
1859年第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在纽约举行,会议围绕黄热病是否具有传染性以及检疫措施的价值展开了激烈讨论。鉴于“检疫措施”在黄热病预防中的失灵,代表们开始质疑“感染论”是否真正有效。同时,许多代表提出应该重视城市卫生的重要性。商业委员会主席哈里斯在报告中指出:“在许多大城市,城市卫生与商业利益存在直接联系,你所生产的食品质量可能就与卫生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城市卫生影响着市民生活,它对公共健康具有重要影响。”[9](P211)随后,哈里斯建议各级立法部门对城市卫生进行立法,并提议任命专人对各大城市中,包括街道卫生在内的六个城市卫生领域展开专项调查,并将在下届会议中发布报告内容。[9](P211-212)著名公共卫生改革先驱格里斯科姆在最后一天的发言中表示:相对于由外部传入疾病的危险,城市内部滋生疫病的威胁更为可怕。至此之后,美国城市公共卫生关注的内容开始由疫病检疫转移到环境治理方面,到1860年第四次全国卫生大会召开时,会议的议题已经全部集中在“城市卫生”方面,有关污水排放以及街道清洁等各种卫生问题的讨论都与疾病建立起直接联系。[10](P105)这样,主张借助清洁环境、消除瘴气,从而实现疾病预防的“反感染论”,开始成为纽约市开展公共卫生活动的指导思想,这为街道卫生改革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政府的责任:纽约街道卫生改革的尝试
从理论上确立街道清洁对于居民健康的重要性,只是纽约街道卫生改革的第一步。改革运动的全面展开还有待于在政府层面对城市街道卫生管理做出变革。1866年2月纽约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为保护健康、防止疫病传播创建大都市卫生区和卫生局的法案》(简称《大都市卫生法》)。这是美国第一部公共卫生立法。根据该法案成立的纽约市卫生局具有广泛权力,它可集中颁布、执行卫生法令,具有对相关问题展开司法审判的特权。纽约持续恶化的街道卫生问题自然成为卫生局的主要治理对象。当时位于纽约市区的屠宰场是城市街道重要的污染源之一。肉类屠宰和牲畜栏冲洗过程产生的大量血水,由于有机悬浮物高,极易腐败,到了夏季更是散发出强烈的腥臭,成为蚊蝇滋生的温床。卫生局规定所有屠宰场必须搬离曼哈顿第40街区以南地区,而且随着纽约市的扩展不断将屠宰场等污染街道环境的产业驱离市区。
与屠宰场整治相类似的治理活动,还有针对城市家畜的管理。从殖民时代起,纽约市民就有饲养家禽满足家庭日常消费的传统。19世纪几次涌入纽约的移民潮中,具有农村背景的外国移民占据多数,这些移民后来尽管身处城市,但多数保留了农村生活的习惯,各家各户饲养牲畜非常普遍。由于缺乏管理,这些牲畜游荡街头,粪便、死尸随处可见。卫生局成立伊始,便承担起对这一街道卫生顽疾的管制。1869年卫生局颁布专项法令,首先禁止牲畜贩子沿街驱赶牛群;同时规定猪和山羊不能在城市任何区域散放;同年还规定向协助捕捉流浪狗的市民颁发赏金。另外,针对粪秽垃圾的管理也在此时全面展开。在卫生局的有效监管下,清道夫开始定时清理旱厕,以往街头粪水四溢的景观大为减少。[11](P68-69,84-85)不仅如此,卫生局还对清道夫进行规范化管理,规定拥有专业手推车和垃圾清扫设备的人员才能获得清洁街道的许可证。[6](P33-35)
街道卫生在纽约市政运行系统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与广大市民的健康直接相关而备受关注,事实上它还是当时纽约市一项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事项。著名城市环境史学者梅乐茜曾对20世纪前美国城市的垃圾管理问题给出较为全面的归纳:“工业革命以前,许多较大的城市就已经开始直接承担基本的卫生服务或将卫生服务外包给私人公司,但是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垃圾收集和处理问题应由私人公司承担还是由政府直接负责仍然悬而未决。起初,通过签订合同或颁发特许状向私人公司购买街道清洁服务更为盛行。”[4](P23-24)因为,私人公司通过外包的形式承担垃圾收集和处理工作后,将大大减少市政府在这方面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市政府只行监督之责即可。于是,这种街道卫生管理模式很早便得到纽约等大城市的青睐。此外,纽约街道管理模式还与城市政治极具关联。首先,获得相关合同的公司可以为选民提供就业岗位;其次,私人公司为了获取合同,贿赂主事官员屡见不鲜;最后,在买入街道清洁服务时,政府官员以换取贿赂或回扣为目的,给出过高的服务出价几乎成为当时城市政客的重要收入来源。然而,私人外包合同的弊端不止如此。由于私人公司的唯利性,许多无法作为农用肥料的无机垃圾由于无利可图,常常无法得到及时清理。加之腐败横行,外包合同可以轻松获取,城市监督机制形同虚设,许多私人公司的工作效率非常低下。1872年州立法机构颁布法律,将纽约市卫生局所承担的街道清洁职责全部转由市警察局承担,以加强对街道卫生的监管。按照规定,市警察局有权吊销那些效率低下的私人公司清洁街道的合同,并自行组织人员进行街道清洁。[12](P17)尽管市警察局在街道清洁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建立在私营基础上的街道清洁系统并没有发生动摇,街道垃圾的清洁工作很快随着80年代人口的增加而再度恶化。 综上所述,内战后至80年代末,街道清洁问题已经在纽约各界引起广泛关注。但是,由于城市政治腐败横行,严重影响城市街道清洁的效率,同时街道清扫体制中私人合同制弊端不断显现,致使纽约城市街道的卫生状况并没有取得较大改观。尽管如此,人们已经认识到,街道卫生不仅是个人的义务,还是市政府的责任。种种迹象表明,由政府主导的更大规模的街道卫生改革即将到来。
纽约街道卫生改革更大规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要归于乔治・韦林的努力。1895年至1898年,韦林在担任纽约市街道清洁委员期间,不仅为城市街道卫生改革摇旗呐喊,更重要的是他将许多前人的环境卫生思想付诸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果。韦林执政纽约的时代,恰逢进步运动的高潮,此时的纽约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一系列城市改革,从揭露社会阴暗面的“黑幕揭发运动”,到轰轰烈烈的社区改良运动,再到禁酒运动和妇女参政运动都在纽约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些针对不同城市问题的改革,分头进行,内容互有交叉,推动着纽约社会的进步,最终在纽约形成了一股改革的潮流。借助进步运动的改革之风,韦林将纽约的街道卫生改革推向高潮,纽约的市容面貌出现巨大改观。这样,纽约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街道卫生改革的引领者,韦林本人也由此成为这场改革公认的领导者。其具体改革内容如下:
(一)调整人员构成,重塑公共形象
韦林上任伊始,首先对街道清洁部(the Department of Street Cleaning)的管理层进行了改组。他看重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组织纪律性,选拔职业技术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和退伍老兵进入管理部门,将那些早先通过政治分赃混入清洁部的人员剔除了出去。
同时,他还非常重视基层街道清洁员的作用。在他看来,街道清洁员的手工清扫,远比运用相关机械更为有效。那些游走于大街小巷的清洁员是广大市民了解清洁部工作的窗口,而他们所从事的街道清扫工作又是市民衡量清洁部工作效果的标尺。因此,韦林一直致力于建立一支高效的街道清洁队伍,并将其看作保证整个部门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在过去,街道清洁员职位,往往是政治机器贿选的工具。从事这一职业者多是初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文化素质不高,好吃懒做,酗酒滋事是纽约市民对街道清洁员的一贯印象。为了扭转街道清洁员在广大市民心目中的不良形象,他对街道清洁员实施“军事化”的管理模式。韦林要求所有清洁员出席“早操”,列队点名,对于那些擅自离岗或者酗酒闹事者处以罚款或者解聘。当然,韦林对于街道清洁员形象最直观的改变,还属其对街道清洁员“白色天使”形象的塑造。他命令所有清洁员在工作期间身穿统一的白色制服,头戴白色头盔。纯白的色彩很自然让公众将清洁员与医生、护士等卫生职业联系在一起,而警盔样式的头盔,又向大众暗示这是一个代表政府,具有执法性的群体。
随后,韦林还每年组织街道清洁部成员列队游行,向纽约市民展现这支清洁队伍的精神风貌。1896年5月26日,韦林带领✡1400名街道清洁员,600名垃✄圾运输人员在第五大道举行盛况空前的游行活动。[13](P19)游行队伍列队整齐,身着统一洁白制服,携带扫帚或手推垃圾车浩浩荡荡前进。这次游行对于街道卫生部形象的改善无疑具有积极影响。这一点可以从游行次日,韦林对所有参与游行人员的贺词中反映出来:
我非常感谢所有参与这次游行的成员……这次游行的成功对于整个街道清洁部的影响将是永恒的。这场游行势必将对公众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些曾经对街道清洁员抱以蔑视和嘲讽的人,现在将向我们投来赞许的目光。可以肯定,街道清洁部已经摆脱了长久以来处在市政机构边缘的地位,我们的工作将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13](P6)
(二)改善员工待遇,提高工作效率
韦林对于街道清洁系统的改革不仅仅停留在内部人员结构的重组以及职业形象的塑造。统一着装、列队游行、严肃纪律等措施固然有助于营建街道清洁队伍的职业自豪感,但是真正提高清洁员工作积极性的最有效办法还在于改善职工待遇。在韦林的积极推动下,街道清洁部提高了清洁员的工资水平,每位清洁员的工资达到每月60美元,这一收入几乎是当时纽约多数技工工资的两倍。此外,韦林还在纽约市首推八小时工作制,这样街道清洁员的工作时间要比当时其他行业的劳动者工时短得多。[14](P108)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韦林还在街道清洁部内建立了一个劳资调解委员会,专门调解街道清洁员的各种不满,防止清洁工人消极怠工或罢工等事件发生。这一做法在美国当时那个阶级对抗尖锐的时代,显然具有前瞻性。
此外,为了提高街道清洁员的工作效率。韦林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细致的职责规章制度。根据规章,所有清洁员所承担的清扫任务都被明确规定。例如,“某位清洁员负责第十街区,两个十字路口之间路面的清洁工作。在其工作时间内,这位清洁员会不停地对路面垃圾进行清理。明晰清扫责任,将方便上级官员进行问责,提高了街道清洁队伍的工作效率”[15]。
(三)强化街道清扫,尝试新方法
从纽约市街道清洁的历史经验来看,能否对这项卫生工作保持长久的热情是决定城市街道卫生取得成效与否的关键。在韦林接受纽约街道卫生委员一职之前,只有主要街道可以获得定期收集垃圾的市政服务,而且承担收集和运输垃圾任务的主体为弊端丛生的私人合同商;街道清扫工作也主要由沿街居民个人承担。韦林上任后,强化了纽约的街道清扫工作。首先,由街道卫生部全面承担街道清扫和垃圾收集工作。其中街道清扫被韦林视为整个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韦林的任职期间,“街道清扫工作占到部门劳动力的60%,占部门全部支出的40%。当时每天约有1450多名清扫人员活跃在纽约各条街道”[4](P56)。其次,韦林将街道清扫服务拓展到城市各个街区,许多之前从未出现街道清扫人员的贫民窟地区也开始享受这项服务。他专门指派了两位年富力强的清洁部官员前往五点区,督导那里的街道清扫工作。[14](P106)他告诫前往五点区的清洁员,对于当地居民的敌意,要保持克制,用自己的行动感化当地居民,从而赢得对自己工作的支持。[15]另外,韦林还将全市划分成若干区域,各区域都有专门的督察人员对街道清洁员的工作给予监督。“当时纽约多数街道每天清扫的次数都可达到二至五次。”[16](P42) 除街道清扫这一职能外,垃圾收集与处理也是街道清洁部的重要职责。长期以来,纽约市区垃圾的处理奉行“眼不见为净”的原则,城市中超过3/4的垃圾被倾泻到远离岸边的大洋中,但是随着洋流运动和潮汐变化,许多固体垃圾又重新聚集在长滩等地岸边。事实上,如何实现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一直是世界各大城市环卫部门探索的主题。韦林在历史上首次将刚产生不久的垃圾分类思想,运用到具体的垃圾收集实践中。他认为将一些仍可使用的垃圾再次利用,不但可以弥补垃圾收集和运输中所消耗的成本,而且更便于垃圾的末端处理。他将城市垃圾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厨房中产生的有机垃圾;第二类为家庭取暖所产生的煤灰;第三类为各种可以再利用的物质,如纸张、衣服以及玻璃瓶等。在韦林的倡导下,1896年纽约市颁布垃圾分类条例,要求每家每户以及商业店铺遵循垃圾分类的原则。按照新的垃圾收集法规,那些不遵守规定的个人将被处以罚款或逮捕等惩罚。[17](P72)
(四)积极推动公众参与
韦林在积极推动街道清洁部展开历史上空前改革的同时,也经常强调市民自身在这场街道卫生改革中的责任。虽然身为市政官员,韦林本人一直积极参与各种市民组织。城市改进协会、妇女健康保护协会等组织都曾留下他的身影。在这些市民组织中,韦林尤其推崇“青年街道清洁联盟”。
进步运动时期,许多社会改革者们广泛认为,“青年人在各种社会改革中的作用至为关键,尤其是那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开始独立于自己的家庭,他们更容易接受新鲜的思想和观念,他们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具有探寻生活真谛和个人价值的潜力”[18](P93)。当社会犯罪率提升、社会道德退化、妓女问题涌现,各种社会改革团体纷纷成立,其中许多团体都非常重视对青少年成员的吸纳,如纽约市民历史俱乐部、道德协会、禁烟联盟等组织都是通过青少年这一群体来树立社会责任感和自豪感的。[16](P178)
作为一位具有进步主义思想的改革者,韦林注意到了青少年群体的特殊意义。他认为建立一个倡导街道清洁卫生的青年组织将推动整个纽约的公共卫生事业。一方面,街道清洁部可以依靠这些青少年发现城市中各种不卫生的环境和现象;另一方面,通过这一组织可以起到教育青年的作用。与此同时,纽约社会中存在大量文化程度不高,甚至不会英语的外国移民,通过学校中受教育的移民子女可以将各种卫生知识带入移民之家。起初,“青年街道清洁联盟”只是卫生监督员指导下,在第十和第十一街区成立的小型俱乐部。但是在街道卫生部的直接推动下,这类青少年组织很快呈星火燎原之势。到1899年,纽约市的“青年街道清洁联盟”已经是拥有75个下级组织、5000多会员的大型组织。该联盟以“保持街道清洁和健康环境为宗旨,每周都会举行有关城市清洁卫生的例会。此外,还经常走上街头协助清洁员捡拾垃圾”[16](P179)。总之,“青年街道清洁联盟”成为纽约城市街道卫生改革中最有影响力的市民组织,其在教育广大市民遵守街道卫生方面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正如梅乐茜所言:“尽管联盟取得的成就是很难通过量化来衡量的,但是其在教育城市居民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4](P63)截至20世纪20年代,费城、匹兹堡以及丹佛等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街道卫生组织。
四、丰富的遗产:未来街道卫生治理的路标
1898年随着斯特朗卸任纽约市长,韦林也很快辞去了街道卫生委员一职,大规模的街道卫生改革很快归于沉寂。步入20世纪后,一些具有进步主义思想的街道卫生委员,如J.F.费瑟斯顿曾试图复兴韦林的改革思想,但是终因坦慕尼厅的政治干涉而失败。尽管如此,20世纪初期,纽约的街道清洁事业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这一时期,卫生工程专业开始兴起,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卫生工程专家开始主导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同样对街道清洁卫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1907年纽约市长乔治・麦克莱伦任命美国公共卫生工程奠基人鲁道夫・赫林组成的委员会对纽约街道清洁和垃圾处理等问题展开了全面调查,为街道清洁卫生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指明方向。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纽约市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深受影响,其市政关注的重点也转移到战时政策方面,街道卫生改革落下了帷幕。但是这场以韦林街道卫生改革为高潮的卫生运动影响深远。
首先,街道卫生与居民健康开始紧密结合在一起。殖民地时期至内战前,零星的街道卫生治理已经在纽约市出现,但是那时清洁街道的初衷多是出于“城市审美”的需要。当多数居民还需为生计而奔波的时候,因“审美需求”而展开的街道清洁远远不能引起多数居民的注意。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随着各种恶性传染病不断侵袭纽约市,以瘴气理论为代表的“反感染论”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感染论”和“反感染论”两种对立病理观指导下的各种街道清洁行动呈现出不稳定性。具体而言,每逢疫情袭来,社会各界对街道卫生✞的关注热情便会升温,而随着疫情退却,街道卫生问题又开始逐渐浮现。19世纪后半期在纽约开展的街道卫生改革巩固了“瘴气致病论”在美国公共卫生领域指导思想的地位。恶臭难闻、垃圾遍地的街道卫生开始与市民健康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一方面,促使更多的市民出于自身安危的需要,关心城市的街道卫生问题;另一方面,明确了城市政府开展公共卫生治理的方向。内战后发生在纽约的这场街道卫生治理对美国城市公共卫生改革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明确了公共卫生的最终目标是要捍卫城市居民的健康。
其次,街道卫生的改善需要政府与市民共同努力,偏其一则废。在今天看来,城市街道的清洁工作是城市政府理所应当的职责,然而历史上却并非如此。内战前,纽约市的街道清洁工作并未被看作是一项公共事务,居民个人承担着房前屋后街道的清扫工作。市政府与私人公司签订合同,授权他们收集并运输垃圾。由于私人公司依靠变卖可作为肥料的有机垃圾获取收益,因此在垃圾收集过程中往往带有选择性。许多无法作为肥料的垃圾堆砌街头。随着纽约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街道卫生问题逐渐凸显。内战后,城市政府在街道卫生方面的职责由监督转向直接干预。韦林担任纽约街道清洁委员期间,市政府全面承担起了街道清扫工作。韦林对于清洁工公众形象的宣传和重塑,更强化了市政府在街道卫生中的职责。此外,韦林重视对广大市民的卫生宣传和教育,以“青年街道清洁联盟”为代表的市民组织开始与街道卫生部联合起来,一道改善纽约市的街道卫生。这种联合为其他美国城市处理相同问题树立了典范。同时,许多其他领域改革的领导者也开始普遍重视青年人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在这场街道卫生改革中,以韦林为代表的城市卫生改革者,还首次将垃圾分类思想应用到实践中。尽管此时韦林所倡导的垃圾分类,其初衷还仅仅是要实现“物尽其用”的目的,但是这一过程却促使纽约市民形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为今天通过垃圾分类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创造了前提。
结 语
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纽约市一直是全国首位性大城市,与其他美国城市相比,纽约较早面临各种公共卫生问题的威胁,同时繁荣的社会经济和成熟的市民社会也使纽约有能力在全国率先开展改革工作。进步时代纽约市所展开的街道卫生改革是美国城市公共卫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反映着这场发生于进步时代的城市公共卫生运动的独特之处。
一方面,纽约的街道卫生改革是建立在“科学”与技术基础之上的,这也是整场公共卫生改革的个性之处。从纽约市历时近半个世纪的街道卫生改革来看,社会中盛行的医学理论对于改革具有重要影响。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以“瘴气致病论”为代表的“反感染论”在医学界以及政府有限的卫生管理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这一理论,街道卫生与居民健康开始建立直接联系,这对唤醒城市各界对街道卫生问题的重视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构成了随后街道卫生改革的主要动力。事实上,从内战结束到19世纪90年代,在瘴气致病论的指导下,美国城市公共卫生改革的重心主要集中在“环境治理”方面,医疗的作用没有受到太多重视。公共卫生改革的策略是整体性预防,改革者认为改善生产、生活的宏观环境就能消灭或预防所有疫病。于是,从城市人口日常流动的重要载体――街道,再到其连接两端的居所与工厂,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环境都成了改革者关注的对象。各种环境治理的实践措施,也都以消灭“有毒”的“瘴气”为目标。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现代医学在美国诞生后,细菌致病论开始在医学界树立权威地位。美国城市公共卫生改革的理论思想发生了转变。改革的工作重心由环境治理被疾病诊断、预防以及治疗等专业方法取代。
另一方面,纽约街道卫生改革还体现着美国城市公共卫生改革,是一场与进步时代社会政治改革存在交叉的管理改革。在进步时代寻求建立社会控制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职权和形象的重塑。纽约市以自身的经历,向其他城市展示了城市政府在街道卫生领域应该管理什么和怎样管理。从这一意义上看,纽约市当之无愧为进步时代美国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试验场。另外,当时的纽约市政府正是借助“公共卫生”之名,将街道清洁纳入自己管理范畴的。它在建立专门性的街道卫生机构的同时,积极与当地成熟的市民社会展开合作,通过卫生教育等形式,树立了“瘴气致病论”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性。借助这些“科学”理论,城市政府寻找到了各阶段行使卫生管理权的合法性基础。也正是借助于这些理论,城市政府突破了美国社会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将公共卫生问题诠释为社会公益,一定程度缓解了个人利益与公共福利的冲突。从而将传统上属于私人管理的事务纳入政府的管理范畴,实现了城市政府对社会整体健康的控制。
[1] Ira Rosenwaike. Population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72.
[2] Ronald H.Bayor, Timothy J.Meagher,ed. The New York Irish,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3] Marin V. Melosi,ed. 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1870-1930, Austin: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0.
[4] Marin V. Melosi. Garbage in the Cities:Refuse,Reform, and the Environment,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5.
[5] Joel A.Tarr. “Urban Pollution:Many Long Years Ago,” American Heritage,Vol.22,No.6,1971.
[6] John Duffy.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in New York City, 1625-1866,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68.
[7] Robert W.Kweit, Mary Grisez Kweit. PeoplePolitics in Urba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2013.
[8] Julie Sze. Noxious New York: The Racial Politics of Urb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Cambridge:MIT Press,2007.
[9] National Quarantine and Sanitary Convention.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Third National Quarantine and Sanitary Convention, Held in the New York, April 27th, 28th, 29th, and 30th, New York: Jones,1859.
[10] John Duffy. The Sanitarians: A History of American Public Heal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0. [11] New York City,dept.of Health,Board of Health, Manual of The Metropolitan Board of Health,and The Metropolitan Board of Excise,June,1869, New York:D.AppletonCompany, Stationers,1869.
[12] New York. Department of Heal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Health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for the Year Ending, New York:The Department,1873.
[13] New York. Street Department. The First Parad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reet Cleaning, May 26th 1896, New York:Martin B. Browm Company, 1896.
[14] Robin Nagle. Picking Up:On the Streets and Behind the Trucks with the Sanitation Workers of New York City, Macmillan,2013.
[15] Hunter Oatman Stanford. A Filthy History: When New Yorkers Lived Knee-Deep in Trash, June 24th, 2013, http://www.collectorsweekly.com/articles/when-new-yorkers-lived-knee-deep-in-trash/.
[16] George E.Waring. Street-Cleaning and The Disposal of A City’s Wastes:Methods and Results and The Effects Upon Public Health, Public Morals, and Municipal Prosperity, New York: DoubledayMcClure CO.,1898.
[17] Matthew Gandy. Recycling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Waste, New York: ★Matthew Gandy,1994.
[18] Daniel Eli Burnstein. Next to Godliness:Confronting Dirt and Despair in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City,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