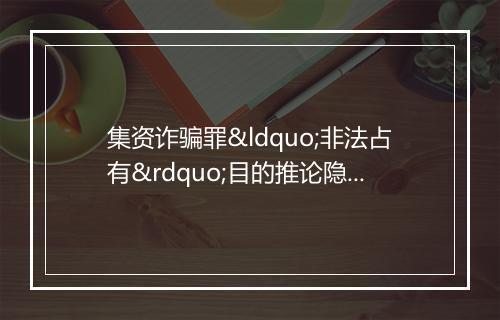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推论隐忧之克服
〔摘要〕现行司法以推论方法认定集资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这存在难以“排除合理怀疑”之隐忧。推论标准重一般而轻特殊(指商事特性)、推论过程重指控而轻辩护是隐忧生成的基本原因,然而现有研究并未触及根本问题。克服现实隐忧的办法是更新推论的思维与技术:观念上贯彻商事思维,关照商事特性;技术上重视反证,坚持正推与反证有机结合,切实解决辩护意见“采纳难”顽症。而对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存疑的案件,按照刑法的谦抑精神分别案情处理,而不是勉强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关键词〕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排除合理怀疑;“吴英案”;商事思维
〔中图分类号〕DF6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6-0110-08
“非法占有”目的是集资诈骗罪认定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因为司法的肯定性认定经常受到“合理怀疑”的拷问。针对这个问题,学者们展开了相关探索,但这些研究没有找到问题的生成之因和提出真正有效的解决之道(见本文第二部分)。本文拟突破现有研究局限,观念上融入商事思维,关照特殊情形;技术上加强反证,实现正推与反证有机结合。期望能够破解“合理怀疑”困局,使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推论结果经得起商事规律的检验,符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一、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推论的隐忧及其原因
(一)推论的隐忧
“非法占有”目的是集资诈骗罪成立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也是集资诈骗罪认定的关键问题。但是,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深藏于内心,一般不愿意真实供认。因此,采用推论的方式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中外司法的共同选择①,也得到学界肯定。如英国学者鲁伯特・克罗斯指出:“推定往往是能够证明被告人心理状态的唯一手段。”〔1〕又如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指出:“主观目的的证明应当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为此就有必要采用推定的方法,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推断行为人主观目的之存在。”〔2〕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决定非法集资犯罪是集资诈骗罪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情况下,由于在刑罚处罚上前者较重而后者较轻,被告人即使有“非法占有”目的也不愿意供认自己的真实内心。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大多也都是以各种借口或者理由否认自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图逃过法律的应有制裁。因此,我国司法对非法集资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判断同样一般是通过推论而非被告人供认获得,而推论的根据是《2010解释》规定的八个认定标准。即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13日《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可以认定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八种情形:(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二)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三)携带集资款逃匿的;(四)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五)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六)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七)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八)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但是,推论的结果常存分歧。我们通过对涉及集资诈骗犯罪的455个案件做样本统计分析后发现,因为“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差异,经常产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认定的意见分歧。其中,公安机关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公诉机关以集资诈骗罪认定的36件(占8.1%);公诉机关指控犯集资诈骗罪,而辩护人主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98件(占21.5%);一审法院改变公诉机关起诉的集资诈骗罪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17件(占3.7%);改变公诉机关起诉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集资诈骗罪的3件(占0.66%);一审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二审改判为集资诈骗罪的1件; 一审判集资诈骗罪,二审改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1件;经重审由集资诈骗罪改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有1件。本文所选取的455个案例均来自北大法宝(V5版本)所收录的1999-2014年7月的法律文书。如此的司法也常遭社会公众或学界诟病,典型案例如浙江“吴英案”。2005年5月至2007年1月,浙江商人吴英以合伙或投资的名义,通过给付高额利息为诱饵,采取隐瞒先期资金来源真相、虚假宣传经营状况、虚构投资项目等手段,先后从被害人林某某、杨某某等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339.5万元。至案发时,除已归还本息38913万元,实际诈骗金额为38426.5万元。经过法院三次审理,均认定吴英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判决构成集资诈骗罪。这引发了社会民众和学界广泛诟病,至今没有停止。因此,“非法占有”目的是集资诈骗罪认定中的一个存在常生质疑的老大难问题,这也说明现行司法的推论方法存在难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之隐忧。
(二)隐忧之因
为克服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推论之隐忧(即难以“排除合理怀疑”),需要找准隐忧生成之因。我们的研究认为,隐忧生成的基本原因有二。
一是推论标准重一般而轻特殊。
集资诈骗发生在商事活动中,通过归纳推理得出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标准既应注重诈骗行为的一般情形,又应关照商事活动的特殊情形。但《2010解释》归纳的七个具体认定标准仅注重前者而忽视后者。如第一种情形中,对集资款用途的认识仅停留在常见的实体性经济,而未顾及商事领域中的非实体经济(如投资理财);对“生产经营活动”与“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逻辑关系认识仅局限于短期的投入、产出与营利,未关注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复杂性:有的经过较长时间的投入可能才有产出甚至营利;第二种情形中对“肆意挥霍”的理解仅停留于普通的民众生活与消费,忽略了基于生产经营需要而必要的高档消费支出;第三种情形中对“携带集资款逃匿”的目的判断仅注重“非法占有”目ณ的支配所为的常见情形,未认识到还可能有因为债权人追债过紧或本人及家人人身受到威胁或伤害而为的特殊情形;第四种情形中对“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仅理解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一般情形,而未考虑可能存在已用违法犯罪所得或者其他资金来源偿还集资款的特殊情形;等等。如“吴英案”中,“无法归还”背后存在投入与产出时间差的特殊性,购买房产、汽车、珠宝等背后存在商业投资的特殊性,“以借还借”背后存在的商业运行习惯的特殊性,司法标准中都未曾顾及。可以认为,推论标准忽视商事特性,为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在标准设计上就埋下了难以“排除合理怀疑”的隐患。〔3〕 二是推论过程重指控而轻辩护。
现实司法中,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推论过程重指控而轻辩护的现象较为突出,具体表现为被告人的合理辩护大多未被法院采纳,而且在裁判文书中对不采纳的理由一般只是笼统否定(“不能成立”之类),无具体理由说明,缺乏说服力。而这种现象在我们的455个样本案例中同样存在:在这些案件审理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定罪异议的有314件(占69%),法院采纳辩护人意见的却只有16件(仅占3.5%)。
从“吴英案”中法院对“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涉及的两个焦点问题(是否随意处理资产、是否存在肆意挥霍)的态度,可以明显看到上述问题。如“是否随意处理资产”问题,在一审庭审中,检方出具了100份署有吴英本人签名或盖有本色集团印章的空白用纸,以示证明吴英经营后期对本色集团的资产并不在意,处置非常随意。〔4〕吴英针对该指控辩称:这些空白用纸是曾被杨志昂等人绑架后被迫签订的,基于人身威迫所签订的内容并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也不能以此作为证据认定“随意处理资产”。吴英还提供了她本人报案后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等材料以示佐证。又如“是否肆意挥霍”问题,吴英在一审庭审中针对公诉方提出的30辆汽车和一辆价值300万的法拉利跑车涉嫌“肆意挥霍”的指控做了辩护:在2006年6月开设了一家婚庆公司,汽车均在同年4月为开展婚庆业务而购买,资产落户都在本色公司名下。而且,法拉利购买后,因为车商以旧车充新车销售,至今未落户,由此引发的纠纷至她被逮捕前还未了结。对于吴英的解释,法院并未进行证据核实,也未进行法庭调查。除此之外,针对涉及其他方面“肆意挥霍”的指控,吴英及辩护律师也提出了反证:“1000万(购买名衣、名表、化妆品等花费400万以及用于坐飞机、吃饭请客、娱乐消费等600万元数目)即使全部算作挥霍,也不是导致集资款无法返还的主要原因,因为1000万仅占到7.7亿集资款总额的1.3%。”〔5〕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全盘采纳了控方意见,认定吴英“对取得的集资款恶意处分和挥霍”,并且以此为由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对于被告人吴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则只是笼统以“与本院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回应。①二审以及二审重审中,吴英和辩护人与一审同样辩称吴英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法院均笼统以“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信”,或者“均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回应。②至于吴英和辩护人的辩称为什么“不能成立”,与哪些“查明的事实”不符,又与哪些“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信)”的具体理由是什么,三份判决书均无针对性分析和说明。
可以认为,推论过程重指控而轻辩护(实质为重正推而轻反证),这为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在推论技术上留下了难以“排除合理怀疑”的隐患。它与前述“推论标准重一般而轻特殊”一起,构成了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难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原因。
二、研究之困
(一)国内研究“未及根本”
学者和实务界已注意到,司法中不少通过推论认定的“非法占有”目的存在难以“排除合理怀疑”的隐忧,而集资诈骗案最为突出。为解此困,学者们从不同的问题切入研究“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但是至今为止,这些研究都未找准问题,自然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国内研究文献颇多,代表性研究成果当推高铭暄教授的“综合反推法”③,刘宪权教授的“主客观结合法”④,古加锦教授的“九种联系
法”“九种联系法”是指,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各种基础事实及其与推定事实之间的九种联系情况进行分析:其一,查明行为人是否通过实施金融诈骗罪的法定行为而排除被害人对其财物的控制并将其财物转归行为人自己控制;其二,查明行为人在与被害人进行金融交易行为时是否存在可能的还款能力;其三,查明行为人是否将被害人的资金用于双方约定的用途;其四,查明行为人是否将被害人的资金用于个人消费、还债等个人用途;其五,查明行为人是否将被害人的资金用于高风险的投资、违法犯罪活动等使资金处于极其不利地位的用途;其六,查明行为人是否具有随意低价处置被害人的财物等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其七,查明行为人是否具有转移财产、隐匿财产、拒不交代资金的真实去向等欲使被害人的资金无法收回的行为;其八,查明行为人是否存在逃匿行为及其逃匿的原因;其九,查明行为人是否属于有能力归还而不归还。参见古加锦《如何认定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法律适用》,2013年第11期。等。这些研究把各种主、客观现象联系起来的思考无疑值得肯定,但也必须看到这些研究存在的局限。“综合反推法”中的“综合”因素――“实施的具体客观行为,各种犯罪事实”――都局限于控方立场而忽视辩方立场,把肯定性事实绝对化而忽视肯定性事实背后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形(否定性事实)。并且“反推”――“运用严谨的逻辑论证来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只是停留于概念层面,对于具体如何“运用严谨的逻辑论证来排除其他的可能性”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问题并未深入研究,因此还没有落到操作实处。尤其对于肯定性事实背后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形、被告方的辩护对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之有无所具有的意义,该理论没有花工夫去发掘。“主客观结合法”中基于客观原因如扩大再生产而投入大量资金导致的暂时“无法返还”或因经营管理不善而破产导致的“无法返还”,排除“非法占有”目的认定,这兼顾了被告方立场,看到了肯定性事实背后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形,值得肯定。但是基于肆意挥霍、携款潜逃等主观原因而认定有“非法占有”目的,则仍然忽视了商事领域肯定性事实背后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形,因为即使如此也可能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有其他还款实力、躲避人身危险等)。此外,对于特殊情形的分析仅停留于“点”(仅对七种情形中的三种情形做了分析)上,而缺乏对肯定性事实背后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形(商事特性)作全面的分析和挖掘,没有解决全部问题。“九种联系法”采用了九种情形的“是”与“否”与非法占有目的“有”与“无”的对接联系法,其中,有的是“是”与“有”而“否”与“无”非法占有目的直接对接,如第四种情形“是否将被害人的资金用于个人消费、还债等个人用途”;有的则是“是”与“无”而“否”与“有”非法占有目的直接对接,如第三种情形“是否将被害人的资金用于双方约定的用途。”这种方法一般可行,但是对于商事领域的某些特殊情形则不可行。如行为人“是”将被害人的资金用于个人消费,但是如果存在确有其他还款途径的特殊情形,就不能直接对接认定其“有”非法占有目的;又如行为人“否将被害人的资金用于双方约定的用途”, 但是如果存在将资金用于更加有利可图事项的特殊情形,也不能直接对接认定其“有”非法占有目的。一般而言,在商事领域,那些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一般情形背后都可能存在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特殊情形,“九种联系法”显然未能顾及这些特殊情形。可以认为,不管是“综合反推法”、“主客观结合法”还是“九种联系法”,就“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一般研究而言,总体上存在的共同问题是重视肯定性事实而忽视肯定性事实背后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形,将正推标准绝对化。具体到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研究而言,除个别学者对个别问题的研究外,忽视商事领域特殊性、忽视被告方辩护意见的情形没有根本改变,对于“非法占有”目的推论隐忧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未真正触及。 (二)域外研究“有向无型”(即有思考方向而无具体模型)
“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也是世界各国刑法中面临的共同难题。〔6〕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域外“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研究与“合理怀疑”理论紧密相关。一般认为只有“排除合理怀疑”,才能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之存在,否则不能。〔7〕但是,对于如何“排除合理怀疑”的问题,大致存在主要基于指控与辩护两种不同立场的研究。主要基于指控立场的研究是研究达到多大肯定程度可以排除“合理怀疑”,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比率量化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等主观要件除了描述性的表达外,可以对肯定程度进行量化,达到定量比率标准的(如60%、70%还是80%抑或更高,具体比率有争议),就是“排除合理怀疑”。〔8〕而把辛普森案主审法官伊藤的理解运用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则是“全然确信”才能“排除合理怀疑”。①主要基于辩护立场的研究是通过研究“合理怀疑”的存在而否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对于“合理怀疑”的界定是研究重点,并且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如“反面定义法”认为,怀疑除两类情形即:(1)基于同情、幻想、偏见、成见、空想、憎恶等个人情感做出的怀疑;(2)基于陪审员因软弱、无能、怯懦而逃避给他人定重罪所出现的不情愿的怀疑之外,都是“合理怀疑”。〔9〕而“正面定义法”认为,基于理性和常理的怀疑是“合理怀疑”。〔10〕“正反结合法”认为,那些基于对证据仔细思考而不是荒唐提出来的怀疑就是合理怀疑。〔11〕此外,有一种“正反有别”的理论甚至明确放弃“非法占有”目的的指控证明,而依赖于反证证明。认为控方只需就基础事实进行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由被告人进行反证证明,即被告人不能证明“合理怀疑”,就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被告人反证证明的程度只需引起合理怀疑就足矣。〔12〕从这些理论可以发现,域外研究固然提供了不少与中国不一样的理论成果。但是就“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实践而言,仍然只是一种宏观、抽象的思维方法研究,而不是微观、具体的操作模型研究。〔13〕尤其是没有针对具体的特殊情形寻找具体操作办法。因此,其研究可谓“有向无型”,这与中国的情形基本一样。从此意义讲,我们并不能从中找到帮助。但是,域外重视对于反证的研究,与中国的情形又显然不同,对于我们研究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三、隐忧之克服
为克服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推论难以“排除合理怀疑”之隐忧,我们需要建立反映商事规律、符合商事特性的思维方式与推论技术。为此,在思维方式上,我们需要改变民商无别的旧思维,代之以民商有别的新思维。具体而言,就是坚持商事思维,关照商事特性。在技术上,改变重指控而轻辩护的旧常态,代之以重视反证、正推与反证有机结合的新常态。
(一)思维更新:贯彻商事思维,关照商事特性
商事即商业经营事务,其本质突出体现为营利性。〔14〕商事思维即反映商事规律、符合商事特性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关照商事领域不同于普通民事领域的特殊性。〔15〕具体到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就是对于某些情形在普通民事领域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在商事领域却不可,因为“占有”一词在民事与商事领域呈现不同的涵义。民事领域的“占有”一般指一种实际控制状态,民间有时指“所有”(即占为己有)〔16〕;而商事领域当事人(商人)的“占有”较多是指“占用”,用作营利(俗称借鸡生蛋),而非“所有”(刑法意义ภ的“非法占有”)。 因此,对于非法集资行为,即便存在某些“欺诈”情形,也要运用商事思维来判断“占有”目的是否为刑法意义的“非法占有”,而不是“一视同仁”。如对集资款在商事领域的“占有”,既应考量实体经济领域“生产经营活动”的“占有”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应考量非实体经济领域(如证券、期货、风险投资等活动)的“占有”仍然可能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又如对“携带集资款逃匿”的“占有”,既要考察基于“非法占有”目的的逃匿“占有”,也要关注其他特殊情形(如躲避催债等)引发的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逃匿“占有”。此外,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涉及的“欺诈”在民事领域与商事领域也具有不同的意蕴:如对“欺诈”的价值定位上,民事领域的“欺诈”被贴上道德标签,是“品行不端”的代名词,被社会予以否定性评价;而商事行为中一定程度的“欺诈”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能够为公众所容忍。君不见现实中常见的广告词:饺子铺广告――“无所不包”、 当铺广告――“当之无愧”、 理发店广告――“一毛不拔”、洗衣机广告――“闲妻良母”等等。这些夸张性的广告宣传在商业领域非但不会被认定为“欺诈”,相反还被冠之“有创意”的美誉而为业界津津乐道。这源于商业宣传需要借助广告这种将真实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并利用信息传播技术这个通道以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17〕商业行为需要创新,如果商业领域中对有创意的“欺诈”与民事领域做相同处理,就可能扼杀创新,让市场失去创新活力。由此可见,如果缺乏商事思维,不加区别地同等看待“占有”与“欺诈”,就会混淆集资诈骗犯罪与商事纠纷或者其他犯罪的界限,导致误判。
(二)技术改进:重视反证,正推与反证有机结合
将关照商事特殊性的商事思维运用到推论技术上,就是要借鉴域外的反证研究思路,改变过去重指控而轻辩护的做法,切实重视反证,并且将正推(即肯定性推论)与反证有机结合,通过“双面夹击”达到证明上的确定性,将是我们较好的选择。如果反证不能证明有“合理怀疑”,那就意味着正推结论已“排除合理怀疑”,具有可靠性。
1.反证之必要
首先,反证是克服正推方法本身先天不足的需要。“非法占有”目的之正推是一个演绎推理过程,即是“大前提――小前提――肯定性结论”的推理过程。“大前提”是推论的根据或者判断的标准,推论结果是否可靠首先取决于大前提。如果大前提不可靠,推论结果自然难以“排除合理怀疑”。我们知道,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是通过归纳推理形成,而归纳形成的大前提天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盖然性。〔18〕这是因为归纳推理“通过整理、概括经验事实,使分立的、多样的事实系统化、同一化,并找出这种系统化、同一化的契机,从而揭示事物的普遍的属性和本质以及必然性、规律性”。〔19〕由于归纳只是对同类事物中的共性进行概括,不关心同类事物中某些个体的特殊性,因此形成的结论只能近似或大概反映同类事物。正推以具有盖然性的结论为根据(大前提)进行推论,说明正推本身就存在先天缺陷,推论的结果也就存在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风险。有了反证,一方面可以从反向的有“合理怀疑”而避免正推缺陷的现实化(反证成立时),另一方面可以从反向的无“合理怀疑”验证正推已“排除合理怀疑”,从而保证正推的可靠性(反证不成立时)。因此,就方法论而言,反证具有保障正推结果可靠性的功能,是克服正推方法自身缺陷的需要。 其次,反证是弥补司法认定标准先天缺陷的需要。假如以“年轻女性在选择男性伴侣时,都倾向于成熟型”的随机抽样分析结论,来推断现实中的女性张某、李某等个体也持相同的性价值取向,那就可能与客观实际不符。同样的逻辑是,将诈骗类犯罪案件的普遍认知套用于商事案件,很可能对于商事案件形成误判。但是当前,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都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文件所确立的认定标准为依据①,而这些认定标准不但存在没有考虑商事特性的先天缺陷,而且都是正推标准,存在反证标准缺失之缺陷。反证标准缺失为具体集资案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埋下了难以“排除合理怀疑”的隐患。有了反证,就可以弥补司法认定标准的先天缺陷,保障“排除合理怀疑”。
2.反证之举要
依前所述,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需要贯之以商事思维,对那些能够引起“合理怀疑”的特殊情形给予足够重视,技术上通过反证予以排除。结合《2010解释》的内容,可以建立与正推对应的假设性反证标准。举要如:第一项认定标准中, 在生产经营中,如果存在长线投资的情形(即经过较长时间的资金投入才能产生效益),就不能仅仅以出现“集资款未返还”的客观结果就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第二项认定标准中,如果是基于生产经营需要而产生的高档消费或自我包装行为或具有投资性支出等特殊情形,应排除“非法占有”目的。如为开展业务而发生高档娱乐消费支出的,为经营需要而购买高档轿车、豪华办公场所的,为投资而购买珠宝、黄金首饰、不动产(主要指商用办公场所、商品房及商铺等)以及具有稳定性回报的政府债券、企业股票的,等等;第三项认定标准中,如果因为出资人非法追索集资款而导致行为人或其家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引发的携带集资款逃匿的情形,应排除“非法占有”目的;第四项认定标准中,如果存在“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而获利并已返还集资款的,排除“非法占有”目的(违法犯罪另当别论);第五项认定标准中,如果存在基于公司、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规范性要求而发生的常规审检、年度财务审计而出现的暂时“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等情形引发的逃避返还资金的,应排除“非法占有”目的;第六项认定标准中,除了“搞假破产、假倒闭”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外,如果出于其他目的(如隐瞒违法犯罪事实、保护商业秘密等)而为的,应排除“非法占有”目的;第七项认定标准中,如果同样存在出于其他目的而为情形的,也应排除“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如“吴英案”,虽然“集资款不能返还”,但是考虑到吴英经营的企业大多在短期内难以赢利的客观现实《华夏时报》报道:“当年吴英投资的酒店、美容、娱乐业,现在都是东阳ย的红火行业,而其购买的大量房产和门面房,至今已经上涨了三倍多,2006年买的商品房价格每平米不到3000元,现在贵的一万多,便宜的也有8000元,门面房涨得就更多了。”可见,对融资行为追诉过早,极可能扼杀正常的商事经营活动。,依据反证假设应排除“非法占有”目的认定。〔20〕此外,吴英虽然有“肆意挥霍”行为(如坐飞机、请客吃饭、娱乐等1000万),但是她有庞大的本色集团的发展作为集资款返还的基础,也应排除“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毋庸怀疑,对于实践中能够引起“合理怀疑”的特殊情形,依据商事思维,通过反证假设进行排除“非法占有”目的,就能确保推论结果的可靠性。
3.反证之保障
全国著名的“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等重大冤案的查明以及“念斌案”2006年7月27日夜,福建省平潭县澳前村17号两户居民家被人为投入氟乙酸盐鼠药而多人中毒,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邻居念斌成为犯罪嫌疑人。该案历时8年10次开庭审判,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终审判决念斌无罪。的戏剧性变化表明:司法者与辩护方构建何种关系对案件走势及裁判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如“念斌案”能够得以扭转,与辩护律师尽职尽责、司法者认真倾听辩方意见具有重要关系。反证本来是发现和避免司法差错的有效途径,但是在我国,“反证采纳难”是一个司法顽症。为改变此状况,一些学者做出了不无见地的探索,如有学者就如何提高辩护采纳率问题提出了“5项保障措施”“5项措施”具体包括: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诉讼结构的优化、法庭的自治和自决、判决理由制度的建立、程序性救济机制的构建。央视法制频道《庭审现场》栏目于2009年4月25日的《亿万富姐受审记》专题报道。参见万茵《吴英亿万富姐的罪与罚》,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126页。,其中建立“判决理由制度”的意见很有直接针对性。〔21〕我们认为,针对非法集资案件“非法占有”目的认定过程存在重指控轻辩护的现状,目前可付诸实践的是改革裁判文书制度。(1)建立“不被采纳”辩护意见完整记录制度,即将被告人的辩护意见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客观完整描述;(2)建立辩护意见“不被采纳”说明制度,即在裁判文书中对“不被采纳”的辩护意见具体说明理由;(3)建立辩护意见“不被采纳”救济制度,即对于辩护意见“不被采纳”又不在裁判文书中具体说明理由的,被告人有权要求补正,裁判机关有义务补正,并且要在制度设计上落实相关权责。同样以“吴英案”为例,如果有前述裁判文书制度保障,吴英及辩护人在二审中提出的辩护意见“未被采纳”的理由将大白于天下,对于“非法占有”目的以及集资诈骗的认定正确与否,都将彰显无遗,不辨自明。如果认定正确,必将取信于民,而不至于遭受社会诟病。
四、余论:司法认定中存疑情形的处理
对于司法现实中某些关涉“集资”的案件,可能因为证据等原因而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存疑的情形,如果以集资诈骗罪认定就存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隐忧。对于这些“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有疑的案件,我们需要秉持现代刑法的“谦抑”精神,分别案情按照“疑罪从轻”(重罪与轻罪存疑时)或“疑罪从无”(有罪与无罪存疑时)的原则进行处理,而不是勉强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仍然以浙江“吴英案”为例。首先,针对公诉机关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指控,吴英本人始终未予承认。并且在辩方陈述环节,吴英曾明确提出反证:如果我想“非法占有”,那就没有必要购置大量的固定资产,我觉得(携)现金潜逃或隐匿更加方便。在辩护方式上,吴英及其代理律师都坚持“无罪辩护”的诉讼策略,也是出于这一真实“主观目的”的考量。即使吴英在长期被羁押,精神几乎处于绝望的时候,她也仅承认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控辩双方的证据质证来看,“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确实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一是对吴英集资行为的界定以“明知无法归还”为由 认定有“非法占有”目的,这忽略了投资与产出的关系,是典型的非商事思维;二是根据其购买房产、汽车、珠宝等行为认定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样是缺乏商事思维,因为购买房产、珠宝属于有利可图的商业投资行为,而购买汽车则是为商(企)业经营之所需;三是“以借还借”是许多企业应对经营资金紧缺的商业惯例,并非有“非法占有”目的,吴英也是如此;四是吴英在经营后期,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困境时,并未选择如携款潜逃等直接“非法占有”的行为,而是积极筹款应对。综合这些情形,认定吴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显然存在“合理怀疑”。鉴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存疑,依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吴英案”以不入集资诈骗罪为宜。 对“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难以“排除合理怀疑”的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可根据具体案情认定为集资诈骗罪以外的其他非法集资犯罪(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及企业债券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擅自发行基金份额类非法经营罪)。仍以浙江“吴英案”为例,虽然本案不宜以集资诈骗入罪,但是吴英行为的非ฝ法吸收公众存款性质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其行为造成了严重结果,而吴英对结果的心理态度明显具有不计后果(放任)的特征。相较于其他非法集资犯罪,吴英行为更加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对于“吴英案”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更妥。
〔参考文献〕
〔1〕〔英〕鲁伯特・克罗斯.英国刑法导论〔M〕.赵秉志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56.
〔2〕陈兴良.目的犯的法理探究〔J〕.法学研究,2004(3).
〔3〕杨宇冠,郭旭.“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中国适用问题探讨〔J〕.法律科学,2015(1).
〔4〕〔5〕万茵.吴英 亿万富姐的罪与罚〔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54-257,126.
〔6〕李明.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规则〔J〕.法学杂志,2013(10).
〔7〕卞建林,张璐.“排除合理怀疑”理解与适用〔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1).
〔8〕〔9〕〔10〕〔11〕赖早兴.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J〕.法律科学,2008(5).
〔12〕张威.论排除合理怀疑的动态界定〔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2).
〔13〕〔美〕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M〕.吴宏耀,魏晓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133.
〔14〕蒋大兴.商事关系法律调整之研究――类型化路径与法体系分工〔J〕.中国法学,2005(6).
〔15〕赵万一.商法的独立性与商事审判的独立性〔J〕.法律科学,2012(1).
〔16〕孟勤国.占有概念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占有制度〔J〕.中国社会科学,1993(7).
〔17〕陈培爱.现代广告学概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25.
〔18〕徐梦醒.法律论证的推论规则〔J〕.政法论丛,2015(2).
〔19〕夏甄陶.认识论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97.
〔20〕陈锋.“吴英身后:民间借贷更甚”〔N〕.华夏时报,2014-05-16(3).
〔21〕韩旭.律师辩护意见为何难以被采纳――以法院裁判为视角〔J〕.法治研究,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