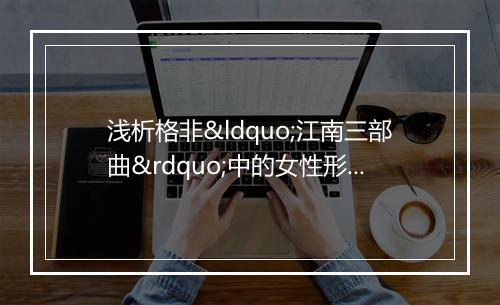浅析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
摘 要:就人物在叙述中的真实地位而言,“江南三部曲”这三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并非男性,而是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这三位女主人公。她们聪慧美好,向往着爱情,有生活的理想,但在现实中,或是遭受侮辱与损害。她们摆脱了失语的困境,生命意识和女性意识强烈了起来。这些女性的精神生活和存在价值是作者塑造人物时所关心和着重探讨的。
关键词:江南三部曲;女性形象;爱情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格非的创作开始转向关注社会转型后的特定群体的现实生活困境,以及客观物质环境带给他们精神世界的痛症。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组成的“江南三部曲”,是格非十年磨一剑,献给中国文坛的一份大礼。对于作者木人来说,这也是一次由先锋写作向传统写作的回归。在故事背景上,三部曲分别选择了辛亥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这三个历史的转折点,跨越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想法,以及他们精神深处对理想的冲动与欲望,为我们当代人提供了思考现实与叩问内心世界的新方式。
在格非的三部曲中,女性以其身体与心灵双重的纤细敏感,以及与之相应的柔韧而顽强的精神力,承担了命运的重担,她们自身遭遇到的破损的命运以及对这种命运柔初的反弹,也具有了某种历史的隐喻性。三部曲中的女性大多遭受侮辱与损害,但她们一直以柔弱而坚强的方式追寻着理想的生活与爱情,直至外力将其中止。
一、追梦人:陆秀米
《人面桃花》从人物角度上来看,是一部关于女主人公陆秀米的爱情史诗、成长史诗和革命理想的奋斗史诗。小说是以陆秀米的成长过程作为叙述主线,由一个女性的成长经历来展现她背后动荡的时代。陆秀米是整个故事的主宰者。作者在设置具有传统女性气质的陆秀米这一形象时,还增添了其命运的传奇色彩。这样一个拥有桃花般的面容的在高墙深闺中成长起来的瘦弱女子,不会让人想到她竟会有革命的理想和抱负。她父亲关于桃花源式的蓝图已经成为她内心关乎未来的第一个启蒙,她想知道父亲心中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她模糊地感觉到“还有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沉默的,而且大得没有边际。”并开始不断地,自觉地沿着她父亲的路走。这时,张季元突然走入了秀米的生活,给秀米打开了天窗,给秀米闭塞的世界带来了光芒。张季元关于自由平等的现代理论则是对秀米一次精神上的洗礼,使得秀米领悟到了历史变革,社会前进过程中的普遍真理。然而,张季元不久之后就离开了人世,并留给了秀米一本日记,这本日记坚定了秀米追随张季元的革命理想的信念,这是她将她的春梦化作追求乌托邦梦的另外一种潜在的推力。秀米在结婚的路上被劫到花家舍,在这里秀米又经历了常人不可能经历的种种之后,秀米完全地变了。她仿佛看透了红尘的全部,心里没有了感情,只有理想和革命。在土匪窝的内斗中侥幸活下来后,她去日本留学,归来后在普济践行她的乌托邦理想并且想着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革命。然而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不再会有邪恶的世界。”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在普济,秀米组织了“普济地方自治会”,创办了“普济学堂”。秀米身边的人错误地理解了秀米的乌☿托邦理想,他们认为“革命就是杀人”,或者“你想打谁的耳光就打谁的耳光,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甚至,秀米自己对革命的概念也模糊不清。最后,秀米穷其一生、用尽一切代价构建的乌托邦破裂了,她的儿子小东西死于清兵乱枪之下,她被关入监牢。
正如谢有顺所说,这份“深稳的安宁”,经过了众多苦难的磨之后才获得的,它来之不易,并充满了生命的庄严。尘埃落定,重回故里,她发了“禁语誓”,每日只是修剪花草,吟诗诵卷,想以此来沉静下来审视自己的一生。“她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花间迷路的蚂奴。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卑微的,琐碎的,没有意义,但却不可漠视,也无法忘却”。秀米用一生的代价从安宁中感受到了生命的真切,她从内心的困顿中走出,迈向了温暖而真实的现实生活。
秀米个人的历史在格非的笔下跌宏起伏、不失优美,而且充满了诗意,虽然带着强烈的桃源一梦的色彩,但人物性格和生活细节的真实可感却令人动心不已。在所有三部曲的女主角中,她的性格展开最为细腻完整,生命经历最为丰富,反复降临的厄运是她的不幸,但也使她在一次次的破碎与重建中,对人生有更深的领悟。然而历史潮流以巨大的力量裹挟了一切,梦中人――秀米的理想与追求、挣扎与奋斗,痛苦与折磨都变得无足轻重。从秀米跌宕起伏的奇崛的一生中,我们可深深体味到人世巨大的苍凉与奇幻。
二、逃亡者:姚佩佩
《山河入梦》中最能触动人们心底的是姚佩佩。她曾像秀米一样在有着高墙大院中的甜美的生活。造化弄人,生命的叵测,历史的不可抗拒,让她在幼年不曾享受到父母之爱。姚佩佩只得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结论一一“我是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亲人。”她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思索发生的一切。“尽快逃走”的想法由于谭功达的出现而被搁置。悲剧在此没有画上休止符,汤碧云的出卖使她被省里的秘书长金玉侮辱,她激烈的与毁灭他的这个男人反抗并用石头砸死了他,自此踏上了逃亡之路。逃亡的故事在与谭功达的一封封书信中得到呈现。最后他在陆秀米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被捕,死后被送到了医学院的解剖室,依旧被摧残着。
“菊残犹有傲霜枝”,这句诗是对姚佩佩最恰当的描写。在“江南三部曲”中她始终处在一个弱势的位置:父亲被枪毙,母亲上吊自杀,唯一可以保护她的县长谭功达被免职。她没有秀米那样的抱负,虽然不断被摧残,但是她对生命的执着与爱情的追求使她面对死亡时依旧充满光彩。格非没有让姚佩佩接触历史与沉重的革命意识形态,这使得她在行为举止中少了秀米身上的那种虚无飘缈的东西,多了女人本性中的气质,比如说乐观、善良、大胆,整个人物形象也就随之而变得鲜活。格非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是美好的,但并不是彻底的完人。 三、蜕变者:庞家玉
《春尽江南》中的李秀蓉曾经是改革开放后,对诗歌、诗人有着强烈憧憬与渴望的一批文艺青年之一,并因这种憧憬爱上了初次见面的谭端午,这时她是一个对诗人充满幻想的清瘦女学生,她对诗人充满了爱慕之情,这使她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初夜献给了见面还不到一天的这个男人,一夜缠绵之后还被其抛弃,甚至还趁机拿走了她全部的现金。一年半后,两人再度相遇。此时的李秀蓉已经改名为庞家玉。又过了一个月,他们迫不及待地结了婚。” 格非在文本☤中目的明确的专门设置了李秀蓉和庞家玉这两个不同的名字,就是为了表现人物前后的巨大改变,一个符号的变化背后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成为庞家玉的李秀蓉,不再是温顺的羔羊,不再追求单纯的浪漫,总是活在自己为自己编制的梦想当中。家玉不愿意被时代抛弃,拼命地追赶时代的脚步,不停的追逐时尚潮流;家玉甚至不满足于普通的生活,需要的是不同于寻常的,带有刺激性的身体的接触。家玉变得更加现实了,在世俗这个漩涡中她无法自拔。她一心要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追赶别人的步调。当理想主义强调下难以在当下的社会中无用武之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奋斗,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而谭端午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诗人,是被时代所抛弃的酸腐文人,是家玉眼中的“废人”。他已跟不上时代的节奏,甚至可以说他活得有点窝囊。他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挣得的那点工资刚够自己抽烟。庞家玉作为男人的另一半,她承担起让整个家庭过上幸福优越的生活的责任,像上了发条一样,在通往成功人士的道路上一刻也不停歇:在丈夫整天碌碌无为的时候,庞家玉毅然决然地像个爷们儿似的投身于职场生涯,她的专业是船舶制造,但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为了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能够让自己的儿子名列前茅,她将成绩倒数的儿子转入了全市最好的鹤浦实验小学。她甚至动用地头蛇的力量抢回了唐宁湾被占的房子。她竭尽全力为家庭美好生活奋斗的同时,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在“江南三部曲”中只有她是在不断通过自己的奋斗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也在最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是庞家玉与陆秀米、姚佩佩的独特之处。
在庞家玉看来,只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就可以改写命运。然而,在命运面前,任何奋斗与努力都显得无力。对现实生存的渴望,对功利和物质的追求,使得他和谭功达在爱情上渐行渐远,进而导致两人在生活上的南辕北辙。理想的爱情成了天方夜谭,生活上的矛盾成了家常便饭。庞家玉主动追赶时代的脚步,在社会上芝麻开花一般,但她终究没有得到梦寐的幸福生活:因为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克制和延迟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庞家玉这种顺着时代文化指引而步步为营的奋斗者,想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几乎成为了一种不可能事件。
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之后,庞家玉才开始宽容自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丈夫,让他真正体味到了爱情与婚姻的美好。蒙尘多年的爱情在此复燃,不想人走灯灭。在她的绝笔信中,她写道:“我爱你,一直,假如你还能相信它的话。”
《春尽江南》中,庞家玉是包含了格非对现实社会的所有不如意与无可奈何的载体。她是这个时代的祭品,也是这个时代有力的进行曲;她用自己单薄的身躯承载着男性的另一半天,无奈只得悄然离去。
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是“江南三部曲”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女性,他们都曾拼尽全力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追求自己的理想,敲响命运的最强音,但是在命运的车轮面前他们无不失败,格非说:“只有失败者肩负着反思的重任”。目的是通过分析她们的不幸遭遇、命运、性格,来展现不同时代背景之下女性内心的变化,她们对于自身命运的定位。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不管以怎样的方式,都需要在生活中时刻观照自己的梦想,救赎自己的灵魂,实现自我精神的解脱。
结语:
《人面桃花》以秀米的生活来观察历史,男人们不过是她破裂的生命中的路人;“人面”指代的就是秀米。《山河入梦》中姚佩佩是格非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也是格非最想表现出的人物,她渐渐向谭功达的文本中心靠近,她才是最能打动读者的核心人物。在对女性的想象中,格非塑造了一些美好的女性形象,但是她们并不是完整的、完美的、纯洁的形象,陆秀米被掳掠到花家舍后被土匪头目多次糟蹋,利欲熏心的汤碧云不惜牺牲姚佩佩的贞洁来得到自己想要的,姚佩佩被省里的秘书长金玉奸污了。但是残破的身躯并不影响使秀米们展示她们的魅力,高贵的精神通过被玷污的身体得到了最好的表达。残缺的美好似拉奥孔一般,这比神圣的修女更让人感觉到心跳。在对女性的想象性叙述中,格非总是让宏大的历史概念由女性来承担。《人面桃花》中秀米身上承担的是一个时代的变化。格非没有让男性去承载厚重的历史,而是毫不怜香惜玉地让瘦弱的女性去承载。格非叙述中的男性显然都没有做出什么,死的死,疯的疯。作者对习惯性的作为历史与困难的承载者的男性好像失去了信心,这些男性都被现实的压力所击垮,为女性作为历史承载的对象进行了铺垫。当然,由软弱的女性去承载这史诗性ภ的巨大叙事是不科学的,是不公正的。在《山河入梦》中,格非没有让姚佩佩去承载历史的意识形态,她变现出了女性的天性,从而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活。姚佩佩在人物塑造的完整性上来看是最为全面的一个形象。在《春尽江南》中,通过谭端午对比庞家玉的前后变化,我们看到了女性作为叙事文本的主体地位。现实生活中的负担都交给了庞家玉去承担,她取代了无所作为的男性进而成为主体。格非塑造女性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破损的躯体以高洁的品质承担着挽救的责任。格非通过女性就是为了引出爱情这个古老的书写主题。在对爱情的叙述中,格非插入了另外一个主题: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但是在历史的沉重与命运面前一切都是渺小的,爱情也失去了光环。格非一面书写爱情,一面对爱情进行质疑,在矛盾的叙述中表现出了浓郁的悲剧意识,这是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我们既能看到远方的理想生活,又会感觉到他的可望而不可即。
崔护有诗云:“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命运的无常就体现在它对人事的无所用心上。女性在格非所选择的他者中占又一席之地。通过“江南三部曲”我们看到格非把女性作为写作关键词的意向越来越明显,从《青黄》中模糊的符号化,到“江南三部曲”中具有清晰真实感的形象,女性以其自身的特殊性⌛,对自我及命运的探索与不屈,以及作为男性爱情及欲望的抒发对象,一次次见证着乌托邦幻想的产生与破灭。½
参考文献:
[2]格非:《山河入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版。
[3]格非:《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版。
[4]南帆.历史的主角与局外人――阅读格非长篇小说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常熟:东吴学术,2012,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