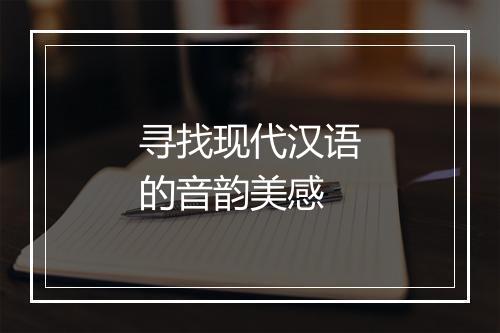寻找现代汉语的音韵美感
寻找现代汉语的音韵美感
诗和歌原本是一回事,互相不分。可是歌唱和表演依赖天赋及训练,不太容易。相比而言,说话和阅读要简单得多。因此,诗逐渐独立出来,不再依赖音色、旋律和肢体语言,而只用语言来展示语言的魅力。诗与歌分离是诗歌发展的主流方向。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是诗的语言,富有节奏和韵律,令人回味无穷呢?
有句话说:诗有别裁。别裁体现在诗歌语言的所有方面。我们从读音、词法、句法、文法四个方面来看诗的个性和特长,看看诗是如何做到妖娆多姿、光彩夺目的。
首先,诗可以堂而皇之地读别音。
语言是发展变化的,无论字形、字音、词义、语法,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语音是其中变化最剧烈的部分。所以,什么是别音比较难于定义。汉语历史悠久,变化更大。像入声的消失和平声的分化,导致如今连四声都与古代不一样。这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常常出现纠缠难办、没有定论的情况。对付这种模糊,我们使用“约定俗成”的办法来对付。
但是诗歌在读音方面有特权。像《论语》《诗经》、乐府、唐诗、古文等各种典籍中,都保留有一些古音。对于散文来讲,读音不是关键。我们用普通话朗读《论语》和《史记》,即½使与古音不符,一点问题也没有。这就好比不同地方的人用不同的方言说话,读音尽管不同,却足以表情达意,顺畅交流。但是诗歌里的古音不好随意更改,因为一改就不合辙押韵,没法读了。这类字中比较著名的,像斜(霞)、儿(倪)、衰(催)、回(怀),等等,都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念远上寒山石径斜、嫁与弄潮儿、乡音无改鬓毛衰、碧水东流至此回这样的诗句,若不恪守古音,该怎么办呢?是依据《平水韵》,还是遵守《新华字典》?这是个真正的难题。在通篇普通话的大背境下,关键位置的关键字要保留远古的读法,是诗歌的特权。尽管有些古音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在各种现代方言中,系统的比如闽南话和粤语,零散的比如湖北方言把斜读成霞,上海话把儿读成倪,可是我们却不在小说散文中这样读。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诗意的“别音”。
享受这样待遇的还有京剧。京剧唱腔源于乡土,保留了很多方言特色,并加以美化,像白、解、街、如、日、时、世、珠、树等字,读法都不同寻常,唱起来特别好听。这是因为京剧在本质上也是诗,诗与剧的关系密切。
在选字用词上,诗的翻新手法更多。“豆蔻”就是十三四岁,豆蔻梢头二月初,描写美丽的少女。“三五”就是三个五,表示农历每月十五,用来指称圆满的月亮。五成了和百、千、万、亿一样的数字词头。在杭州西湖的曲院风荷,有一块石碑上刻有藤野先生写的白居易诗: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寻常”还可 以当数字用。杜甫《曲江二首》: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一联妙处何在呢?从字义上看,寻常就是平常、普通;从对仗规则上解,则寻常必须是数字,才能与七十相对。它们的确是数字: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同一个词,在同一句话里,居然可以正义、别义兼用,拐一下弯,造成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对于用词,诗人还有一种巧妙手法,那就是在看起来不该用的地方用,形成强烈的通感效果。像“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曾经引发了长久的争论。
在所有这些手法中,典故的运用是诗人创制新词最得力的手段。辛弃疾用典用得多,以至于被人讥为“掉书袋”。我们来读他的《破阵子》,几乎句句是典:“掷地刘郎玉斗,挂帆西子扁舟。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燕雀岂知鸿鹄,貂蝉元出兜鍪。却笑泸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试手不?寿君双玉瓯。”当中比较冷僻的典故有两个:“貂蝉兜鍪”和“泸溪如斗”,用的分别是南朝齐将军周盘龙和南朝宋大将军宗悫的故事。周盘龙年老不能戍边,还朝任散骑常侍。有一天世祖和他开玩笑说:“你戴貂蝉(近侍的冠饰)比起兜鍪(战盔)来,感受有什么不同吗?”周盘龙回答说:“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宗悫晚年为豫州刺史,可是典ฉ签不买账,经常违拗他。大将军无奈叹息:“得一州如斗大,竟遭典签慢待!”“如斗大”平平常常三个字,却传达出深厚微妙的含义,非典故不能表达这种效果。
任何人,只要具备足够的文史知识,都可以运用这种手法批量制造诗歌专用词;而典故的运用,又让诗人可以为几乎所有他要表达的想法找出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多个端庄典雅、文采斐然的别名,恰如其分地融进千变万化的上下文环境中——这样的技巧,从韵文传播到散文,从古文扩散到时文,书香馥馥,袅袅不尽。
从句式上说,诗可以不遵循标准的语法。只要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哪怕“病句”也是好诗。“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登楼》),按正常顺序,这两句应当写成“花近高楼此登临,万方多难伤客心”。“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屈原《离骚》),按通常语法应当写成“吾既有此纷内美兮”——我既拥有如此深厚的内在禀赋。颠倒是为了强调或者押韵。仿别音、别字、别词的例,我们不妨称这样的句子为“别句”。若是使用屈原的语法,“寻找现代汉语的音韵美感”就要写成“现代汉语的音韵美感寻找”,相当♒别扭。可见散文通常是不可以这么颠倒的。
诗可以无比罗嗦,“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乐府民歌《木兰诗》),东西南北兜一圈,不厌其烦;也可以极其简略,“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出塞》),把相隔上百年的事情捏到一块儿,还省去一半;可以酣畅淋漓,“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韦庄《菩萨蛮》);也可以结结巴巴,“编,编,编花篮”(民歌《编花篮》);可以颠三倒四,时间、空间、逻辑、情感的顺序统统不走,“半夜三更贼吠狗,公鸡拖起狐狸走”(儿歌《颠倒歌》);也可以精密严谨,胜似学术论文,“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宋子侯《董娇娆》)。诗可以不知所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锦瑟》),这样的诗,你就是读上一百遍,依然ท迷糊,难以索解,脑海中勾勒不出一幅清晰的画面。诗还可以根本不讲理。赤壁明明在嘉鱼,东坡先生的《念奴娇》大笔一挥,轻轻巧巧就把它挪到了黄州,成就一段佳话。对于这件事,有人这样说:“不是坡公两篇赋,如何赤壁在黄州。”只要圆融不滞碍,诗人小小地违背一下常识亦无不可,可以接受。我愿意把这种现象称为诗的“别调”。
别音、别字、别词、别句、别调,千样姿态,万种面貌,总之诗有特权,可以打破条条框框,不完全遵守通行的规则。有了这个特权,诗人可以创造性地运用各种语言素材,尽情施展拳脚,尽一切可能地呈现出有个性、活泼泼、妖娆动人的精美作品。“晴窗早觉爱朝曦,竹外秋声渐作威。命仆安排新暖阁,呼童熨贴旧寒衣。叶浮嫩绿酒
初熟,橙切香黄蟹正肥。蓉菊满园皆可羡,赏心从此莫相违。”(刘克庄《冬景》)读上一遍,两遍,三遍,我们甚至都不用弄明白它到底讲什么,就可以背得滚瓜烂熟,脱口而出,真正琅琅上口。这就是儿童启蒙多读多背唐诗宋词,有助于开发语言天赋的理论基础。
《书卷集》诗选
春天里娇嫩的野蔷薇
春天里娇嫩的红蔷薇,
缀满了废花圃边腐朽的棘篱。
根根花枝在晨光里摇动,
勾起了我孤单的伤感情绪。
我为什么不是闪亮的雨丝,
一直落进花蕊的深扉,
把花儿最内在的机制润湿,
绽开她花芽原基里沉睡的艳美?
细雨打湿了单薄的白蔷薇,
她们在水塘坍塌的对岸开了一地。
我啊如这片荒僻的郊野,
被她的盛大所激发鼓励。
为什么我不是尖刺或者锯缘复叶,
千样皱折,和花瓣挨在一起,
在这万物繁茂的春天,
陪衬她禀赋的宁静飘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