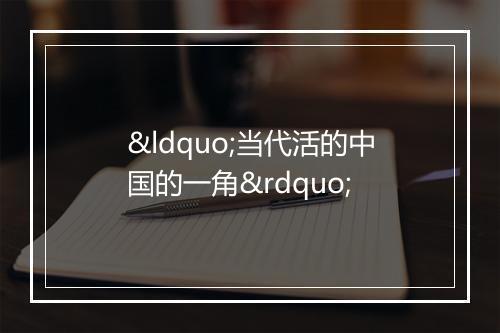“当代活的中国的一角”
一、“常识”之外的农村经验
不妨以向本贵的《盘龙埠》为例,看看与喧嚣而审美的文学“1980年代”很隔膜的农村,农民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当年的经济主义已经在显露出新的暴力逻辑,新贵们开始报复以前作为弱者时遭受过的屈辱(闹餐事件和砖厂竞争);昔日变着法子侮辱妇女的人民公社的贺干部,仍然是1980年代乡供销社的神通干部贺采购;水电站的头头为了外地专家领导的参观,或者“上了级别的人物”和外国游客观看人工瀑布的好奇,可以擅自拍板开闸放水,造成下游农民生ว命财产的损失却延例成习;女性的漂亮“身体”(女推销员、公关小姐们),开始成为一些面临破产倒闭的工厂、包括农村小砖厂换取起死回生的商业手段;新起商人(王有文)以行贿说服贺采购,凭空垄断了穷人最后经济依靠的河沙的运输权,乡亲们虽有怨言也只能痛苦地接受;农民(李二宝)因为家有长期病人已经堕入了赤贫境地,女儿又因为这样的连带原因悲惨自杀;对于知识的追求(王有金的“写书”),在全面的窘迫中备受了亲人和乡邻们的露骨的讥嘲,等等。我们是不是从中看到了一些让人不安的东西,却又感到它们似曾相识?隐去具体的小说人物姓名,这些实际上已经涉及了1990年代的许多事象,如何从1980年代演绎而来的问题。
尽管《盘龙埠》从时间上看仍不免是一种后来的追述,不过做到这一层纯朴真切的写实再现,已经算是颇不容易。作为延续,我们可以从向本贵的《苍山如海》里看到上述诸多事象在1990年代的呼应形态。比如,“男女作风”出问题的伍生久,仍然是宁阳县实权在握色欲不改的工业局局长;省级高干为了吃鱼腥草,致使挖鱼腥草的农民被毒蛇所咬伤;原本是民间盛事的龙船赛,需要为某高干的随兴观看让千万人在烈日曝晒下延宕达数小时;与某些官员有勾结的建筑商朱包头,对事故砸死三个民工丝毫不以为意,直言“如今有钱什么事都好办”;以及库区搬迁补偿款在市民和农民之间分配的大幅不平衡,它是明显的差别化方式,也使农民在极度节俭和自苦中显得愈加沉默和忍耐;甚至农民在《苍山如海》中的故事基本只能以并列的方式展开,而无法有机地与市民的故事相融在一起,虽然它们源自同一个“大局”的事业,等等。
1980年代到底如何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脱胎而来,具体它又如何向1990年代逶迤而去?至少在农民文学的讨论领域,这中间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应该说至今仍然不是很清晰。向本贵的小说,却给予了我们许多有益的提示。
从这样的路径,我们还会发现《盘龙埠》里有两个情节,几乎堪称1980年代农村变化的极其微妙的寓言。一是王有文偷运木头出台铺木材检查站遭遇检查的事。在这里,凡事懂得给好处的偷运者王有文、接受贿赂但仍然“没有要抬横杆的意思”的检查员小袁和“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却知道在最恰当的时机中止检查的矮子站长之间,有着太多让人回味不已的东西。
他们好像久经默契,见怪不怪,但是又都淡定入戏,分寸和火候拿捏得煞是精准。这是1980年代习见的农村基层权力、私人攫利者和国家监控规则之间绝妙的张力场景,当时的乡村到处可以亲见或者听闻到类似的故事。但是我们可以觉察到,它们与《乡场上》《哦,香雪》《人生》《陈奂生上城》《爸爸爸》等确实颇不相同。
它们是不是浪漫主义的文学“1980年代”还相对陌生的乡事?小说中另一桩引起不小轰动的事件,是王有文在后村口古柳下贴出的《告父老乡亲书》(坐车要收费)。结果,以前亲热的乡邻们开始冷嘲;父亲王昌龙训斥并动手打了儿子;当然,王家兄弟也早就对凡事“讲钱”感到了不怎么适应。但是王昌龙却回答不出儿子的“你在这么大热天抛汗脱皮地在山上挖桑皮”不就是为了想钱,和“你们什么时候从中南门过渡不要那两角钱”的问题。
这表明乡村里久已有之的“情义”伦理与新兴的经济主义之间,开始出现了危机。耐人寻味的是,有文自信的质问,意外地受到了二哥有银的支持,他以集体时代遭受过ฅ的痛苦生活的记忆,和新时期个人认真的努力也没有得到情义报偿的经历作为证明。一时间大家面面相觑,“一个个都默不作声”。
我们不应该忘记,当年激越地为经济主义声言的时候,王有银的理由正是我们最为经常地听到的两种诠释逻辑。难能可贵的是,恰恰当时经济力量最为低弱的王有金,反而在窘迫中坚持提出了自己的反质疑,“按你说世界上没情没义了,那么我肚子饿了,又没钱,向别人讨红薯吃,别人就不会给,应该向我要钱的”。同样地,王有金的话也将两个弟弟问得哑了口。
在这里,我们隐隐瞥见了1990年代某些思想反思的影子。“讲情义”和“讲钱”,究竟孰是孰非?这个艰难的话题在小说中延续了超过半数的章节,直到小说终篇。但是小说的阐释,却不是1980年代挽歌气息的“老”输给“小”,“旧”输给“新”,也不是1990年代暴戾袭人的“利”比“义”合理,“成功”比“失败”正当等逻辑。
在现实的教育下,乡亲、贫富、父子、兄弟等各方面都不知不觉地从最初的坚硬自信的立场后退了一步,最终达成了“情理”的和解。这是小说作者在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中,最为自然地表露出来的思想性力量。
三、重新发现失落的乡村权威
不过,向本贵在新世纪以来的农民小说里似乎“愤怒”了。上述的县、乡、镇、村干部中的许多人,在他的新作品里已经迅速地蜕变。比如,微薄的扶贫物资,甚至不及民政干部们一顿饭从赤贫农户家吃回去的,最后使得村➳妇刘兰香自杀(《农民刘兰香之死》);乡党委书记利用贫困农民的感恩心理,暧昧地向他们推销昂贵的橡皮船,并且不顾他们的性命安危强行让其全家一起示范漂流,憨老一家终于逃走(《憨老的光荣任务》);乡干部为了给县干部行贿急缺资金,就巧为设局诱农民兴赌,再继以围抓、没收和巨额罚款(《赌局》);镇党委书记不惜污损前恋人的清白声誉以自保,同时却无耻地强逼她为不切实际的政绩工厂捐献巨资,目的仅仅为了成就他个人的前程(《碑》);更加突出的是,六千多人的苦藤河乡赤贫如洗,很多农民家里没有被子,破败的木屋有的不能全其四壁,甚至有的村全村没有一顶蚊帐,也没有一所小学,但是丁安仁、顾家好、顾家富、匡兴义、宁占才们却骄奢淫逸横行乡里(《乡村档案》),等等。
在这一部分县、乡、镇、村干部的身上,官僚政治化的威权而不是“权威”,重新成为了基层乡村破坏性和压抑性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原先的政治干部和基层权威合二为一的现象已经发生了改变。――在这种特殊的语境里,真正的乡村权威们在哪里?向本贵的小说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了这个代偿的系列。
他们是《苍山如海》中平坝村兼任砖厂厂长的郝支书、高崖坡村至死没有忘记奉养五保老太的村支书张守地,《赌局》中的黄土垭村兼任砖厂厂长的村支书赵同兴,《碑》里舍命捐资为乡亲们建桥的平民奇女子田美秀,《乡村档案》里赢得农民普遍尊重的大岩村支书莫胡子和竹山垭村支书全安,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乡村权威们当初与干部身份重合的职阶出现了明显下移。这是不是表明了作家对于农村和农民命运的某种忧虑和愤懑?小说中还出现了自发集资办厂(《苍山如海》),自发集资修桥(《碑》),自发盟誓的乡约(《赌局》),自发公共议事(《乡村档案》)等典型的乡村民间社会自下而上形成新的权威的过程。
它们是新世纪农村和农民真正的希望所在。当然,这里也隐藏着另一个作家没有提及的问题,即农民在果然能够富裕之后,由于新的经济和身份的差异等,他们必然会表现出对于弱者或者公义事业支持力的差异甚至矛盾。到那时,上述乡村权威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如何才能重新召唤起农民们的一致同意呢?……
余 论
诚然,向本贵的小说不是没有它自身的某些薄弱之处。少数的生活细节可能因为作者记忆模糊,事实上略有失误。如《乡村档案》中写到了大礼拜小礼拜的休假制度,这是相当早期的事;而行贿和受贿的人一样要被判刑,又是特别晚近才出现的。
这两者均不与小说中的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的时间相合。他的小说也特别注意经营“故事”,有时很接近反腐或者侦探小说(尤其是《乡村档案》)。当然,结构颇佳的故事,也使得他的诸多中短篇小说确实成为非常耐读又发人深思的佳作。
无论是《苍山如海》,还是《乡村档案》,虽然有惩治腐败的干部、农民也备受鼓舞的情节,不过消散在故事之中的思考可能是:如果不是伍生久,或者丁安仁€、顾家好这样低一层级的干部腐败了,而是一把手或者人大代表、甚至纪委书记也被腐败了的话,故事的意义又将落脚在哪里呢?而根据新时期以来的地方民生新闻,特别是1990年代至新世纪,这种情形虽说并不多见,但确实不止一次地曾经出现过。我们在这类故事的阅读中反复地萌生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或者是,“为什么他们反复地可以?”另如,从诸多迹象看,近数年以来农村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新的乡村权威似乎已经在诞生,旧的权威身份其实正在从乡镇村干部的身上移开去;一系列新的法规以及实际的乡村经济关系,也使得少数昔日有些骄横的乡镇村干部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能再恣意妄♪为了,或者至少换成了更加隐蔽的方式,等等。
这些是向本贵的小说创作可以更多留意的方面。无论如何,向本贵的小说对于今天的年轻的读者、批评者,甚至一部分研究者来说,它所代表的丰富鲜活的乡村经验和批判,几乎堪称一部活的中国乡村的历史。在农民小说的范畴内,它们使我们“看见”了很多非模式化的东西,这是我们能够继以思考的坚实的前提。
曾镇南先生曾经称向本贵的小说代表了“当代活的中国的一角”(《向本贵中篇小说漫评》,《芙蓉》1999年第5期),实际上确实不是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