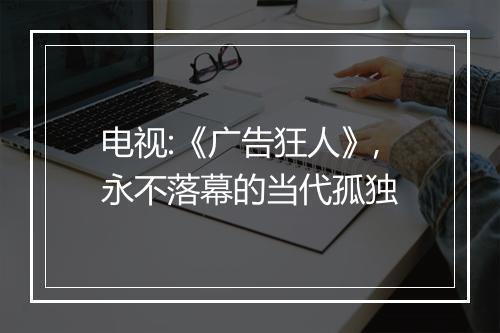电视:《广告狂人》,永不落幕的当代孤独
自2007年首播,《广告狂人》共计获得68项艾美奖提名及15座艾美奖大奖,被《滚石》杂志在内的诸多主流媒体盛赞为“永不过时的经典”。 美国的招牌
从2007年7月到2015年5月,《广告狂人》走过了漫长的7季,大幕徐徐落下。随之落地的还有9年来每集片头那个从摩天大楼上徐徐落下的唐的黑色剪影,如今这个身影终成了纽约地标TimeLife大厦的门口的唐・德瑞普长椅(Don-Draper bench)――下落的仓皇和无助重回洒脱,无畏地舒展着身体,肆意延伸着手臂,依旧是不能再熟悉的唐的背影,充满自我矛盾,沉静寡言,一招致命。
哪怕是那“叮”的一声铃响之后,灵修音乐转成为英国乐队New Seekers的《我想给世界买瓶可口可乐》(I'd like to buy the world a Coke)才做结了全片。令人惊奇的是,这两段乐曲不仅是听觉上平顺相连,连出现在可乐MV里的女孩子们,也一如那些伊沙兰中心里波西米亚风格的嬉皮女子,素面朝天,辫子里扎着美丽的丝带,同样也在绿草如茵的山顶,不同肤色、性别、宗教的漂亮年轻人,每人手里拿着一瓶可口可乐,他们随着音乐舒展摇摆着身体,忘情唱着:“我希望教会世界唱歌,跟我一起唱,唱出完美的和声,我想要给世界买一瓶可乐,从此与之相伴。”
曲终人散,最挥之不去的还是唐那暧昧含混的微笑,没人能准确说清那个瞬间唐的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即便最后一季的剧情里,我们随他穿越了大半个美国,堕入空虚的汽车旅馆幽会,误入愤怒的基督教家庭,与一群可怖的同类相食主义信奉者喝酒,甚至看他遭遇热衷小偷小骗少年却把自己的凯迪拉克转手相让,你不曾有一秒钟怀疑路上的唐渴求着忘却与逃离的真诚。尤其当伊沙兰中心互助小组里的莱奥纳德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如何疏离于同事和家人,甚至臆想自己成为冰箱黑暗中的不可见之物,唐上前紧紧拥抱了他,与他一起哭泣。唐总是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把握这样强烈的情感,并让一切都看上去诚挚动人。
这也不是唐第一次展示他苦楚的真诚。他曾为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真诚相待的女人(梅根)而结婚;他也试着和自己的大女儿萨丽坦白了有关自己的过往;他的真实身份是迪克・怀特曼(Dick Whitman)早不是城里的秘密;他甚至昭昭然做起成瘾者――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性纵欲者、重度酒精依赖者。但唐的天赋在于,他用最快的速度抵达全新的“我时代”(me generation),任何形式的骄奢软弱都能够被赋予正当理由,只要你可以诚实坦白。并且他重新抓住了那条当下的广告语送给他的新老板们,于是我们的英雄已经在新的征途,用世界和平的口号卖起糖水,并由此一手去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只是无论是“二战”后高速发展的美国经济,还是黄金时期的广告业,一切蓬勃向上都无法更改这样的事实:唐仍是那个雷蒙德・卡佛笔下的孤独的美国人。甚至如果我们将唐当作一个新兴中产阶级的符号,也许更加说明问题,他是消费社会中文化焦虑的完美化身,从死ย亡焦虑(幸运牌香烟)到家庭解体的焦虑(柯达相机),如今通过可口可乐,唐完成了自己的杰作,一个有关美国式童真的想象,他清理了整个上世纪60年代的伤痛嘈杂,民权运动、越南战争、暴力暗杀如此等等,就像在那条可乐的广告里呈现的,未来像是一个美丽而年轻的加州女子,素面朝天,动听歌唱着苹果树和蜂蜜,本真如初有如婴孩。“唐更像是一个美国的弗洛伊德式的象征,甚至足以作为那些比如符号学的毕业论文题目,他的男子气概,他的资本主义特征。唐是整个美国的招牌。”《纽约客》剧评专栏作家艾米丽・努斯班(Emily Nussbaum)如是写道。 女性主义教科书
反而是唐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发生着惊人的巨变。皮特、佩吉和琼,他们都不再是剧集开始时的样子:琼放弃了让她束手束脚的甜心老爸,开始了。自己的生意;佩吉接受了斯坦的表白,迟到的真爱的一幕虽然多少有些俗气,同时多少让人遗憾着这个离经叛道的纽约女孩终止于一个通俗的爱情喜剧,但伊丽莎白・莫斯(Elisabeth Moss)出色的演绎确实也给佩吉画上了一个动人的句点;不管罗杰和玛丽的午餐玩笑背后是甜蜜还是裂痕,此时此刻的浪漫已足够;势利实际到有点不讨喜的皮特,却收获了看起来最完整的成功人生,携妻带女奔赴另一个完美的工作;贝蒂平静地在桌边吸烟,萨丽在一旁洗碗,你再也无法计较这个女人的虚妄矫情,却几乎要为死亡面前她的美丽和端庄举杯致敬。
时光呼啸而过,幸运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更加坚强,更加透彻,甚至更合乎道德伦理。与其余描述上世纪60年代的影视作品相比,《广告狂人》没有集中在那些时代中最耀眼的激进主义者,或者嬉皮士身上,相反这里的每个人恰恰是理查德・尼克松所言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是焚烧募兵卡片的反抗青年,也不是老实地躲在格子间里午餐的麻木工薪族,他们智识优异,勤恳地经营着自己广告营销的手艺,以此作为安身立命在野蛮商界的武器。同时他们也不乏偏见,比如对于雇用黑人雇员充满了抵触,也从未对女性有发自内心的尊重,甚至那些同样优异的女人自己也仍在心底犹疑着对自己的看法。 从9年前开播之时,便有人已经为了《广告狂人》中强烈的性别歧视和男性特权怒发冲冠,刚从秘书学校(Miss Deaver's Secretarial School)毕业的佩吉,芳龄20岁,相貌平平但身材丰满,当她踏进史特灵・库柏(Sterling Cooper)广告公司,立即被一群言语轻薄的男人围住,被他们无礼挑逗一番。这一段场景,已足够令广大女性观众目瞪口呆,如今她们所深以为然的是如果佩吉愿意,可以把整个公司的男人们告到破产。毕竟如1980年美国第一次将性骚扰定罪并纳入司法范畴的史实,早不是人人都清楚的陈年往事。
9年之后,《广告狂人》无疑已经是近年来最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电视剧之一。曾以《黑道家族》大获成功的制片人和编剧马修・维纳(Matthew Weiner)毫不讳言自己在争取女性观众上所付出的努力。身为男性编剧的维纳毫不讳言,在构思《广告狂人》的阶段,对于整体人物建构最重要的两本书无不围绕女性,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by Betty Friedan)和海伦・布朗的《性和单身女孩》(Sex and the Single Girl by Helen Gurley Brown)。“开始我去读它们,为的是研究故事的历史大背景,毕竟这些都是经典的作品,改写整个美国历史的女性圣经,但令我惊讶的是,它们不仅是历史,我觉得的确很多东西是改变了,但也不是一切都改变了,我知道这些鲜明的女人到今天也会闪耀。”
但维纳始终强调的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电视剧”和“有关女性主义的电视剧”有着本质意义的区别,《广告狂人》始终审慎警觉着的便是成为后者。比如佩吉,从第一天走进麦迪逊大街上那栋气势磅礴的办公楼开始,她不知女性主义为何物,她的脑子里全是惴惴不安,她被办公室总管琼的优雅自信惊得哑口无言,又因为自己浓重的外省乡土气时刻暗自难过,她不知道如何反驳皮特对自己是阿米什人的取笑,却在唐宿醉后说她该去主动取悦皮特的时候,礼貌而肯定地说:“我不想看上去不那么合作,但是我必须这样么?”乃至经历过大大小小的糟糕的感情生活,她选择从始至终像是一个女性版的唐一样,把不可告人的秘密藏在身后,倾情于工作,从唐的门徒,到唐的竞争者,甚至是唐的上司。
“佩吉想要成为老板,她拥有唐所拥有的全部野心,这也是为什么她可以成为最先锋的女性的原因。”编剧维纳解释,“甚至她都没有意识到,在当时的年代和社会,她本来是不被允许拥有那样的野心的。”
倒是自信优雅,对自己的性感风情了如指掌,并且☒深知如何最大化利用其优势的琼・海瑞斯,竟在佩吉工作的第一天如此告诫她:“如果你无往不胜地证明自己正确,你会被驱逐。你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处理琐事的秘书,仅此而已。”甚至远不及佩吉的是,她总是如此羞涩迟疑于抓住那些传统意义上或许不属于女性的机会。当负责电视部门的哈利请琼帮助收集作品反馈的时候,她出色胜任了新的工作,并且乐在其中;但是当资金允许,哈里却很快为这个岗位雇用了一个“合理”的男人,琼的扮演者克里斯蒂娜・亨德里克斯形容,“那是一个无比失落的时刻。琼的自信和脆弱都令人心碎”。
或者也是因为深谙自己的美貌,琼更难割舍那些比如美满婚姻之类的“石器时代的期盼”,直到那段开始于强暴的表演性婚姻陷入僵局,琼却发现自己怀上了旧情人罗杰的孩子。“和英俊医生格雷格的婚姻对琼而言,确实像是一次觉醒,重新的审时度势。”克里斯蒂娜说,“她意识到自己从前期待的东西或者并不是她所真正需要的,也不是自己所真正擅长的事。于是她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她对于家庭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
琼开始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的价值远超过一个“毫无意义的秘书”,她越发无法忍受那些来自男性的轻佻挑逗,更渐渐对那些总是因为自大而冲破底线的男人们失去耐心。直到那间只有她自己名字的事务所成立,她身体力行了歌莉娅・斯坦纳姆的金句:“最终,我们成为那个我们想要嫁的那个男人。”
尤其没有流俗于《绝望主妇》或者《欲望都市》这样的女性故事的是,编剧维纳没有夸大那些“闺蜜”等女性情谊的作用。正像是唐、罗杰、皮特这些孤军奋战的男人们那样,对于欲望和消费组成的纽约城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冷漠,《广告狂人》中的女人们同样深有体会,并且她们有足够的心胸和气度相互欣赏,☯也有相当的明智保持距离――当从麦肯离职的琼为自己野心勃勃的新事业以叙旧为名打电话给佩吉时,佩吉惊喜于琼的问候,转而便用更富效率的职业态度问起重聚的目的。
“我总是从一个人的内部开始去考虑角色,”作者维纳说,“所以每一个人,不管对错,他们为自己的阶层、童年、职业性别种族所塑造。无论是佩姬还是琼,她们都是毫无自知的拓荒者,迫不得已地打破那些理想主义者们视为目标的边界,甚至那种时代性的性别期待。并且她们孤军奋战,她们的勇敢注定了这会是事情本来的样子,我只是想呈现这些本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