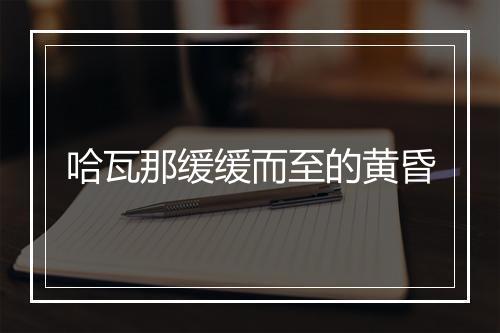哈瓦那缓缓而至的黄昏
在海边的马拉贡大道行走,七翘八裂的人行道上,遍地都是滑溜溜的青苔,还要时刻提防窨井盖子不翼而飞后留下的大洞。这又让东跳西踮、本来未免凄惨的行走变调为简易伦巴舞般的欢快。
马拉贡是一条长达8公里的防汛堤岸,事实上,不管你在哈瓦那城中心的哪个角落,闭着眼一路北行,总能抵达马拉贡,它从哈瓦那的老城一直延伸到阿尔门达雷斯河口。这条防汛堤以北145公里左右的陆地,就是美国领土。51年前古巴导弹危机时,马拉贡成为一条漫长的战线,到处是高射机枪和大炮,还有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古巴的政局自革命胜利以来一直相对稳定,人民相对安稳地生活着,偶尔乱一乱,吵着要去美国,也是基于经济而非政治上的原因。
这条在涨潮时全然挡不住潮水的防汛堤,风平浪静时,只文静地行使着类似外滩情人墙的功能,上面坐满了正在亲吻的情人。在他们的间隙,垂钓人勉强找到了落脚处,还有那些不管不顾欢奔在防汛堤上的孩子们,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吹着很有可能从美国旅行而来的风。
当地人管这条防汛堤叫哈瓦那的公共沙发。那么,滨海一带就是哈瓦那的客厅,面对海峡的那一排街面房子就是客厅的墙纸,被飓风和岁月摧残得不成样子。当你以为这些房子已经长久没人住了,在玻璃都已经不知所踪的窗户上却哆哆嗦嗦地晾出了红红白白的内衣裤。行使着大使馆功能的美国驻古巴利益代表处是这条滨海大道上维护得最好、也最没有风情的一栋火柴盒式多层建筑,它通常被百来面高高迎风招展的古巴三色国旗遮挡着。倘若古美之间发生摩擦,国旗会全部换成肃杀的黑旗,为通常安详的哈瓦那客厅平添一些戏剧张力。 “为了革命胜利,向首都进军”
我在总统饭店散放着舒适藤椅的露台上等候朋友安娜的表弟胡安。这个离海不远的老饭店让我想起上海的浦江饭店,有很多历史名人光顾的照片可以炫耀,但掩饰不了垂垂老矣的内核。
卡尔扎达街上,一群年轻人正走向古巴国家芭蕾舞学校,在学校对面有个广场可以踢足球。他们都很时髦,用着手机,还有种猫王派头的复古时髦,飞机头,粉红太阳镜,鲜艳上装,身材奇瘦。那个足球场其实是个被抽干了水的喷泉池。一切市政建设在刚规划时都野心勃勃,设想喷泉池里会水声叮咚,人行道会平坦宽阔,儿童乐园的器械上油漆会闪光,可是就像ฃ国家建筑师最初理想主义的乌托邦难免会滑向自己也无法预料的政体一样,现在,喷泉池是干的,人行道坎坷不平,儿童☯乐园里连螺丝也都会有人顺手牵走。
两个哈瓦那少年在空荡荡的街道当中打着棒球,一个投球,一个接球,就这样一起向前推进,位移和打球都没有耽误;3个孩子正在帮大人推着一辆老爷车,它需要助推才能发动;一对老夫妇手挽手走过,另一只手都各自擎着一根没有任何包装的粗大灰白的面包,远远看来像是掉了刺的狼牙棒。一个面容严肃的老妪跟在他们的身后,她右手托着一盒奶油蛋糕,说一盒并不确切,因为这个直径10厘米左右的圆蛋糕就放在一块硬纸板上,赤裸在加勒比午后的金光下。
这些面包和蛋糕都来自卡尔扎达街上一家国营面包房,得凭一本配给簿才能购买,价格自然是便宜的,只有自由市场的1/10左右,也因此门口总有长龙。面包房的玻璃窗上贴着振奋人心的标语“alaCapitalporelTriunfodelaRevolución”(为了革命胜利,向首都进军),带着所谓热带社会主义者与生俱来的乐观和亢奋,似乎是要给为食谋的老百姓打气。 我对1959年革命的回忆很快就被停在总统饭店门口的一辆雪佛兰Bel-Air打断。这辆哈瓦那蓝的老爷车好像直接从艾森豪威尔年代慢悠悠地一路行驶过来。从车门里走出来的不是一个头戴礼帽、身穿三件套的冷战时代特工,而是一个面容黝黑、头发卷曲锃亮、身穿牛仔裤和笔挺衬衫的古巴小伙子。他径直向我走来。我突然意识到,他就是我正在等待的人,胡安・马蒂内斯。 “古巴制造,美国进口”
之所以和哈瓦那人胡安有这样一个约会,是因为朋友安娜・马蒂内斯交付给我一个任务:给她在古巴的叔叔带点钱。美国政府现在准许国民每季度向他们的古巴亲属汇款500美金,但安娜觉得,让我亲手把钱交给他们会是个有意思的体验。当时正好是圣诞前夕,她说:“体会一下圣诞老人和特蕾莎修女同时附身的感觉吧!想象一下,这个在生活中挣扎的家庭直接拿到这些钱将多么激动!”
安娜说她堂弟胡安会来酒店取钱。“胡安是我叔叔的私生子,你知道古巴男人的,突然有一天叔叔就把他带回家了,全家就当他是自己人了。事实证明,他还是全家最讨人喜欢的一个。”当时,我正坐在安娜在旧金山的家里,品尝着她特意做的古巴名菜RopaVieja,一种用番茄酱汁煮的碎牛肉,配上黑豆子和黄米饭,还有炸木薯。我点点头,难怪古巴人有句俗语,“Loquelavidameda,coje”(不管生活给予我什么,悉数拿下)。
安娜的父亲提交出国申请后,成了国家敌人,如同任何放弃革命的人一样,被称为“Gusano”(虫子)。他被剥夺了在案头工作的权利,只能在田间劳动。最后,出❥国申请总算获得批准,安娜父母带着她哥哥和肚子里的安娜先去西班牙呆了两年,然后辗转抵达了旧金山。安娜因此很认同在奥巴马就职典礼上献诗的古巴诗人RichardBlanco,因为他们都是“古巴制造,西班牙组装,美国进口”的古裔美国人。
安娜的父亲后来在邮局工作了20年,英语仍然不很利索,退休后移居佛罗里达,可以离哈瓦那近一点。因为当年出走不易,安娜的父母再也没有回过古巴,害怕一旦回去就再也出不来,但他们一直兢兢业业地给古巴的亲戚汇款,接济他们的生活。 底特律的怀旧博物馆
交给胡安的一叠欧元,他将兑换成可以在本地买很多硬通货的古巴可兑换比索(CUC),类似于我国在1995年停止使用的外汇券。在总统饭店的货币兑换柜台,你能看到那些从墨西哥或者加拿大辗转偷偷入境的美国人在排队,拿的是欧元而非美元,因为在古巴兑美元要交10%的惩罚性税。
古巴人其实最喜欢美国游客。美国人大方又带有怜悯心,因为不少是非法过来的,所以更加珍惜;而那些合法的,通过教会、学校或文化交流项目过来的,更是带着救世主般悲天悯人的心绪。小费好像天女散花一样四处飘洒――为那首他们已经听出老茧的街头吉他弹唱《关达娜美拉》,为那些和他们根本没有相像之处的铅笔速写。即使他们最终决定不给钱(多半因为零钱用完了),他们也会充满歉疚地说“I'msoSorry”,好像他们得对美国政府对古巴超过半世纪的贸易禁运负责似的。事实上,古巴政府和不少民众的确把本国渐进性失明式的经济状况归根于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喜欢计算因为这种封锁导致了多少多少亿美元GDP的损失,最后得出一个“美国禁运导致古巴贫困”的结论。
胡安小心地将美国亲戚送来的钱放进口袋,然后扮了个鬼脸,“所以古巴人民都说,美国人是我们最可爱的敌人。”我们喝了一杯咖啡,就坐上了胡安的坐骑。当我爬进车里,深陷入皮革椅后,就得小心地挪动屁股,以使龟裂的皮革不至于戳痛屁股。另外,整辆车只有一个手柄,负责摇动所有的车窗,交由司机掌管,这也使你可以专注于路边风景。当胡安将汽车启动时,我才发现仪表盘上竟空空如也。
胡安是从父亲那里得到这辆车的,而他父亲又是从他爷爷那里继承来的。这辆车来到马蒂内斯家时是1955年,买的是新车,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固定资产投资――六十多年后,这辆“美帝”机动车依然在为他的孙子带来现金流。尽管起初它并不是以谋生工具进入这个家庭的,第一任主人曾经驾驶它,和美国人一样,坐在汽车电影院里看好莱坞电影。
1960年,卡斯特罗政府结束了和美国的短暂蜜月,古巴以经济改革为名推行国有化,没收美国人资产,导致美国与其断交。1961年,古巴政府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外交和贸易的联系中断,同时也留下了15万辆美国车。50年代是古巴♀作为美国销金窝的年代,其进口的凯迪拉克、别克和德索托车的数量曾位于世界之首。
胡安的父辈和胡安们自己造机器来制作各种汽车零部件。如果拆开一辆克莱斯勒,它的汽油缸很有可能是只塑料桶。古巴人总是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或来自黑市,或来自海外亲戚。类似于美国的craigslist.org,古巴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www.revolico.com和www.cu.clasificados.st),其服务器在国外,胡安说,“我们古巴人用它们来找到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一辆古巴小汽车上,往往体现出一种经济禁运下的生存模式:古巴灵巧的机修师傅会在Chevy的铁壳子里,装上苏联的Volga引擎以及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在这辆所谓的Chevy-Volga车里,美国、古巴、苏联和中国放下种种意识形态芥蒂和睦相处。美国五十多年来对古巴的禁运造就了或大或小的奇迹,大而言之,不发达的工业活动让古巴成为世界上最绿的国家之一,这让囊中羞涩的古巴男人除了唱歌跳舞和喝喝朗姆酒之外,能有一件正经事可以消磨大量的工余时光,让修车成为棒球和调情外,另一项全民娱乐活动。何况,一辆经自己摆弄后重新奔驰上路的车,也意味着某种失而复得的珍贵自由。 2009年9月,劳尔政府向一直以来非法经营的出租黑车颁发执照。胡安记得自己在11日一早,就赶到了交通部门口排队,填写将私人汽车改为出租车的申请表,并最终领到了已停发10年之久的私人出租车执照。1990年代,正值古巴因苏联解体而面临的经济“特殊时期”,缺少汽油使公共交通一度瘫痪,政府曾放开私人汽车载客,但到1999年10月即停止。然而这并不能阻止那些家传老古董车走向街头赚面包钱。当时的胡安们都冒着罚款的风险,驾着美国老爷车继续非法拉客。
拿到执照后,胡安的出租车业务合法了,不过他营业时基本不打表,他说:“一切都将由市场决定,供需双方自然会达成一个双方满意的价格。”我敢肯定胡安并没有学过西方经济学,但他们都在社会大学里研修过这门市场经济课。
胡安开车送我到了CafeLaurent餐厅,他从来不知道住家附近还有这样一个被《纽约时报》推荐的哈瓦那热门餐厅。这种私人餐厅在古巴被称为Paladar。1990年代初,个体餐厅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在古巴却还处于地下非法状态,直到1993年开始经济改革,私人餐厅才合法化。Paladar食物水准起伏不定,这通常取决于他们的“mule”,也就是为餐厅带货的人是否能将食材和佐料及时从佛罗里达海峡的另一边捎来,这也给其菜单带来了某种莫测性。
CafeLaurent坐落于Vedado区的一栋上世纪中期建成的5层居民楼的顶层。在晚间要找到这家藏身小区深处的餐厅毫不费力,只要抬头仰望,一栋栋昏暗的楼房中,赫然有那么一栋的顶楼灯火辉煌,露台上还有白色纱帐在飘扬。居民楼的内装是苏式的,显然是革命胜利后兴建的预制板式公房,电梯声音震耳欲聋,四面都装了镜子。
屋内的墙上糊满了1950年代的报纸广告,而露台上的那些白色纱帐很有当代迈阿密泳池边遮阳篷的感觉,从屋里走到露台上,就好像革命从未发生过。一ด切关于私营经济的尝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和现任的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矛盾态度有关。
劳尔对中国的改革模式很感兴趣,1997年访问中国时和朱F基交谈甚欢,还意犹未尽地邀请朱F基的资深顾问到哈瓦那和古巴高层开了几天会。
美国针对古巴移民有“湿脚/干脚”政策,漂泊在海上算“湿脚”,而从你踏上美国国土成为“干脚”的那一天起,满一年就能申请并拿到绿卡。按照古巴改革前的规定,离开古巴11个月,古巴国籍失效,却还来不及取得美国身份,面临两头不着港的风险。现在则可以笃悠悠等到美国绿卡,再决定回不回古巴。这让胡安开始蠢蠢欲动地设计起他的未来生活:先想办法出境,美国每年发放给古巴申请者的约4万个签证如果没他的份,他就去和美国接壤的第三国,比如墨西哥。只要把那双大脚踏上美国国土,就基本意味着绿卡到手,万一不适应美国生活,也有抽身而回的余地。这比想方设法自制小舢板从海上偷渡的风险小很多。
胡安清楚地记得1994年那个炎热的夏天,还是少年的自己踩着中国支援给古巴的自行车,经过马拉贡所看到的情形。那年,“特殊时期”中饿坏了的古巴人通过各种途径逃离古巴。8月5日,古巴军方拦截了4艘企图逃往美国的渔船,引发了哈瓦那人在马拉贡海滨大道上的骚乱,是1959年以来最大的一场群众示威抗议活动。胡安被乱石打破了头,自行车也不知所踪。他撩开刘海,让我看前额上仍然隐约可见的疤痕,说这就是自己不会考虑乘船逃往美国的原因。 次日,卡斯特罗亲自前往马拉贡,向大家保证,“如果你们自己选择要走,政府不会阻止。”随后,人群欢呼“菲德尔万岁”,一场本来气势汹汹的抗议活动,最后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哦,至于CafeLaurent的菜式,我点了一个用“SalsaEspejo”酱炒的猪里脊。那个神秘的“SalsaEspejo”,翻译成中文是不明就里的“镜子酱”,吃上去除了酸甜的味道外,完全没有什么镜子般的魔力,猪里脊则明显炒过了火候,有点难以咀嚼。我听从了胡安的建议,没有点牛肉。胡安说,吃牛肉,你还得到国营饭店,牛肉在古巴可是稀罕物,一般只特供给政府涉外单位,私人餐厅即使可以到黑市高价买牛肉,质量依然比不过国营餐厅。可是,我发现胡安还是默默地点了两份主菜,牛肉丸子和洋葱牛肉。毕竟对本地人来说,眼前的牛肉,永远是最好吃的牛肉。在配额供应体系里,每个古巴人每年只能分到两三次牛肉,一次仅半磅。这促成了黑市非法宰牛的兴旺,为此政府只能对那些非法屠宰的人处以重刑,你会听到古巴人认真地对你说:“非法杀头牛判的刑可能比杀个人还重呢。” 哈瓦那最后一个黄昏
在哈瓦那的最后一个黄昏,穿着初夏的衣裳,我从总统饭店出来,向马拉贡大道北行。马拉贡大道和G街交界处那幢玻璃好像随时就准备稀里哗啦掉落下来的大楼,是古巴外交部。门口没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把手,只有一个腆着大肚子、一直在看手机的草绿军装大叔寂寥地守在门口。那些在建设时设想的喷泉或小池子,现在变成一个个盛放垃圾的大型容器。
我对外交部对面的何塞・马蒂体育场异常感兴趣,每天长日将近时,总会去那里转一转。这座当时想给人带来强硬未来感的苏联风格体育场,现在就像一个被早已奔往外星球的飞船永久遗弃的港口。顶篷颇具科幻气息的看台早已进入风烛残年,周边墙上用油漆刷着“摇摇欲坠”的字样,提醒人们慎入。然而,一个年轻人一溜烟钻进看台下的一个破洞,他们把它作为了更衣室。里面有粪便的气味。青年迅速更完衣,加入足球场上的战团。
此时,何塞・马蒂体育场的近处弥漫着儿童学骑自行车的叮咚铃声、拳击手出击的砰砰声、女孩们捉迷藏的欢叫声、男孩们挥棒击球的梆梆声;稍远处,是小伙子们在足球场的奔跑呼喊声;再远处,就是来自佛罗里达海峡的浪花越过防汛墙,在人行道上摔得粉碎的痛呼声。而那些孤独地绕着足球场的长跑者是沉默的,他们一次又一次打你身边经过,以近乎相似的间隔时间。大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并不需要观众鼓掌或喝倒彩,而看台上也的确没法坐人。再过十来分钟,我在古巴的最后一抹夕阳就会永久消逝。
我珍惜此刻的哈瓦那,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乐园,而不仅仅是一个20度就好像是冬天、人民每天排队买面包、波浪平均高过防汛堤三倍、年轻男子想着乘慢船偷渡、漂亮女孩难免要被当作妓女的城市。
我拦下了一辆正好从我身边经过的Cocotaxi,和马拉贡平行着,我们最后一次向哈瓦那老城进发。我戴上耳机,找到“美景俱乐部”那些老枪们的歌,是的,这是此刻我最需要的告别曲,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经济改革,不论过去,亦不谈将来。我要去老歌手依伯拉海姆・费热(IbrahimFerrer)曾挽着太太徜徉过的那条哈瓦那老街:镂空拉花的铁门,粉蓝斑驳的外墙,不知所措的流浪狗,坐着或站在门口的邻人……
依伯拉海姆唱着:“送你两朵栀子花,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我仰慕你,我的爱人,把爱心给它们吧,我俩心心相印……”我的视野就这样无可挽回地从凋零的街景转向了流金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