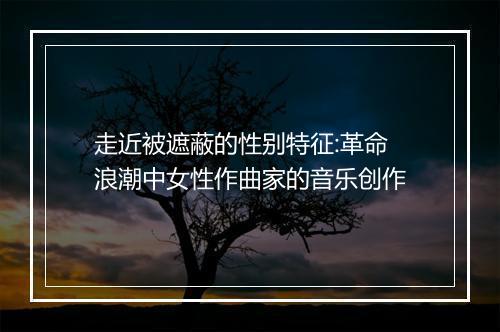走近被遮蔽的性别特征:革命浪潮中女性作曲家的音乐创作
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大都和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民族命运纠结个人生活境遇成为音乐创作的主流。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西方音乐技法和音乐观念开始传入中国。从担负启蒙任务的学堂乐歌开始,音乐从古代的政教和娱乐功能,开始具有启迪民众的社会价值。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一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都极大地影响着音乐创作。女性走出闺门,融入社会,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出现了第一批真正意义的女音乐家。她们用音乐表达对革命的支持,对新生活的赞美,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古代女性的独特之处。
在封建旧制濒临灭亡的20世纪初,中国社会更迭变幻,外敌入侵的战争环境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契机。获得新生的女性以被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她们走出千百年来被封闭的闺阁,以独特的力量参与到民族解放的滚滚浪潮中,由此催生了第一批女性公共知识分子。其中,革命诗人秋瑾,声乐教育家、作曲家周淑安,钢琴家李翠真、顾圣婴,琵琶演奏家、民族音乐学家曹安和,词作家安娥等以不同方式参与社会的音乐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紧张的革命状态。以延安鲁艺为中心的根据地音乐创作成为后来音乐界的旗手,在红☤色革命浪潮中出现了第一批真正意义的女作曲家群体,黄准、寄明、李群等的音乐创作为女性音乐史增添了新的一笔。改革开放以后,女音乐家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流行音乐、电影、电视音乐、艺术音乐领域都活跃着一批优秀的女性,如二胡演奏家阂惠芬,声乐表演艺术家、教育家周小燕,指挥家郑小瑛,流行音乐作曲家雷蕾、谷建芬,先锋派作曲家刘索拉,专业作曲家陈怡、张丽达、李一丁等,其中有些甚至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女性作曲家,虽然性格特点与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但其创作不可避免地与革命浪潮密切相关,表现出创作主体社会化、创作题材革命化、文革以后多元化的特点。
一、创作主体社会化
作为儒家大一统思想的组成部分,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就像枷锁一样禁锢着女性的身体和心灵,它烙守宗法礼教,强调女性的卑弱地位。在历史上的许多朝代,女性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束缚,没有自主权,只能服从社会的安排,并将父权社会的性别观念内化为自我意识,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整套规范。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生育的纯粹性,女性的生活被规范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封闭空间里,沦落为男性的私人财产。虽然中国古代社会不乏能歌善舞、从事音乐表演的女性,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影响下,普通女性的音乐才能既不被重视,也不受鼓励,在音乐史上留下笔墨的并不多。能称得上音乐家的女性的社会身份往往比较特殊,她们或是深藏在闺阁之中的名媛贵妇,在闲暇中偶尔消遣,或者是在宫廷、官宦、青楼中卖唱的歌伎,用血泪挥洒有限的青春,她们被分为不同层次,服务于以皇帝为首的男权社会。
近代中国的女性解放是在男性思想家的竭力倡导与大力支持下展开的。1989年的戊戌变法可以说是中国女性性别意识初步觉醒的起点。此后,滚滚而来的革命浪潮带来了男女平等的性别意识,被解放的新女性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她们勇敢地走上街头,与男性一起寻找民族解放的道路。尽管参与音乐活动的女性并不多,但是与封建社会中的女音乐家相比,她们大多数都带有较强的社会意识,如,由著名诗人、民主战士秋瑾作词的《勉女权歌》慷慨激昂地唱出了中国女性争夺妇女权力的心声:我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坐同侍,恢复江山劳素手。
秋瑾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身份广为人知,同时她还是学堂乐歌时期最早使用简谱填词的女性。作为变革时期的女诗人,秋瑾早期作品具有中国古代闺阁少女的雅致、婉约和伤感,其后期作品却体现了现代女性强烈的平权思想。尽管留给世人的歌曲并不多,但她具有鲜明社会意识的作品开创了中国女性创作的新风尚。当然,若非清末民初的革命浪潮,若非西学渐进带来男女平等的新思想,若非兴女学的教育培养,秋瑾的音乐创作自然不会从个人情感的抒发转为对广大女性忧患的焦虑。
℃1927年,我国第一所高等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李群姐妹、黄准的创作来看,莎莱创作的《怒吼吧,鸭绿江》《纺棉花》,李群创作的《大生产》《快乐的节日》《我们要做雷锋式的好少年》《歌唱毛泽东》等歌曲都带有鲜明的革命意识,黄准为电影《红色娘子军》创作的歌曲《娘子军连歌》更是成为中国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象征。此外,寄明在1960年为电影《英雄小八路》创作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于 1978年被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这些带有鲜明革命意识的女作曲家大都是共产党员,她们不仅配合形势创作和演出,也同男性一样劳动,一样革命,一样参加土改剿匪及社会主义建设。她们早年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文艺干部,不仅在创作上又红又专,在思想上也带有鲜明的革命意识。如黄准本名黄雨香,因名字比较柔弱,后改为较为男性化的黄准。寄明原名吴亚贞,奔赴延安后改为寄明,意思为寄希望于明天。
女性在追求中性甚至男性气质和行为方式的同时,性别意识被强有力的政治话语所化解,进而消融于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之中。当然,女作曲家对革命题材的热衷并不意味着对男权价值的简单认同,而是特殊历史时期个体意识在群体意识中的消解。看似平等的做法与封建社会的两性观并无本质差别,因为无论是沉鱼落雁的美女,步履踊珊的小脚女人,还是舞刀弄枪的女战士,立场坚定的红卫兵,女性形象都要符合男性社会的政治和审美需求。在某一历史阶段,女性形象一旦被主流文化所追捧,就会很快成为社会大众竞相追逐的目标。其结果是,女性为适应男性社会所需要的一切,逐渐在被塑造的形象中失去了自我。
战争时期的音乐创作思维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愈演愈烈,在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等政治运动中,主流音乐依然继承延安时期的思维方式。女作曲家的创作也基本延续了革命时期雄浑激越的风格,倾向于阶级对立、民族解放的题材。瞿希贤创作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红军根据地大合唱》《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歌曲,李群的清唱剧《英雄库里申科》、辛卢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等都选取革命题材,音乐风格也都带有鲜明的革命印记。
三、文革以后多元化
由于政治、文化的原因,中国现代女性的成长历程曲折而艰难。文革以后,女性的音乐创作更加多元,表现在: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活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音乐工作者恢复自由,老一辈女作曲家谱写新的乐章,在艺术音乐领域继续自己的音乐梦想;电视、电影等多媒体的普及为女性提供了新的舞台,部分作曲家开始将目光投向流行音乐和电影、电视配乐,并赢得了极大的声誉;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大批有为青年重返校园,高等院校中接受过专业音乐教育的作曲家将自己的事业拓展到了国外,中国女性作曲家终于真正浮出地表,走向世界舞台。
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不同,中国女性没有经历性别反抗便直接获得了解放,反叛性的缺失使得革命浪潮中的女性创作实际上依附于政治活动,缺少对自身性别的反思。改革开放后,社会整体人性回归,女性话语、女性意识、女性经验等成为女性创作的主要特征。如,曾在圣约翰大学英语系接受西式教育的瞿希贤,其声乐创作反映了一个时代创作观念的转变。 瞿希贤曾是革命的推崇者,在争取解放、激荡人心的时代里创作了许多应时之作,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刚毅雄健、气势恢宏,充满了强烈的政治热情。但对革命充满激情的瞿希贤在文革中也没有摆脱厄运的纠缠,在监狱中6年多的非人待遇使其音乐创作产生了很大变化。合唱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作曲家一样,在文革前流行、文革中被批判,文革后被视作经典而恢复名誉。关于这首作品,秦西炫先生曾有一段回忆:
瞿希贤80岁后,创作逐渐停笔了,但她的思维一直很清晰,曾和我谈起,一些业余合唱队要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她极力劝阻不要唱了,特别是2005年在她的作品演唱会中,唱返场节目时,不少听众高喊: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因为她事先已和指挥打了招呼,硬是没唱。她说此曲是在当时政治形势卜写的,现在形势不同了,再唱是误导。此曲收录在《飞来的花瓣瞿希贤合唱作品》中,她在注释中写道:收入此集作为历史足迹厂
中国人的政治热情在文革时达到顶峰,其个性意识在此阶段亦受到极大的压抑。在文革期间失去创作权利的作曲家,其创作激情在文革后重新点燃。在这个时期,对政治意识的消解和对人性的描写成为许多作曲家着力表现的主题。瞿希贤曾说:我感到惭愧,因为50,60年代我的歌曲与当时的各项政策的关系太紧了,所以现在一首一首地没用了。我歌颂过三门峡,可水库本身是失败的。我歌颂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可我到甘肃时看到饿死了人。因此,文革以后瞿希贤创作最突出的变化是消解了原有的宏大叙事,并通过新的方式呈现个人经验,与政治密切联系的作品几乎没有了,而表现人性人情的作☃品占有明显位置。《把我的奶名儿叫》《飞来的花瓣》等情真意切、细腻委婉的艺术歌曲,根据内蒙古民歌改编的质朴深情的无伴奏混声合唱《牧歌》等都表现出浓厚的人情味,蕴藏着博大无私的母爱和师生情谊。在改革开放之初,这种温情的表达令人耳目一新,如梁茂春所言:80岁以后的瞿希贤,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心,从武器和功利的观念转到审美和抒情的观念。这是一次经历了炼狱之后的真正的升华。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全面转型。随着商品经济、消费主义及全球化的强势涌入,文化丧失其整合的功能,人们普遍失去政治热情,个人情感体验成为作曲家竭力表达的内容,这在流行音乐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文革及其解冻后的一段时期内,流行音乐颇受非议,但由谷建芬创作的抒情歌曲、李一丁和雷蕾创作的电影、电视配乐很快脱颖而出。这些作曲家创作了许多类型不一、脍炙人口的歌曲,并借助媒体迅速传播,如谷建芬表达游子思乡情怀的《那就是我》《绿叶对根的情意》,表现朋友之间友谊的《思念》《歌声与微笑》,表现母亲情怀的《妈妈的吻》《烛光里的妈妈》,❅表现生活美好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世界需要热心肠》,表现校园生活的《我多想唱》《校园的早晨》,及表现对祖国热爱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以上这些流畅而又饱含深情的作品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成为一代中国人难以忘却的回忆。
在专业作曲领域,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开始开放,女性受教育的机会逐步增多,专业音乐教育逐渐繁荣,象牙塔中的学生如饥似渴地补充着十几年来被压抑的学习热情。在80年代巨大的音乐变革中,女性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男性依然掌管着主流音乐界,但越来越多的女性积极加入作曲家队伍,在新潮音乐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些女性接受过严格而正规的作曲训练,见多识广,大部分都有国外深造的经历。如先锋派作曲家、作家刘索拉除了电影配乐、歌剧、交响乐、音乐剧创作外,还在爵士、摇滚、蓝调等先锋音乐方面进行制作。中央音乐学院首位女作曲硕士陈怡获奖学金赴美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先后担任美国两个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两所大学的全职作曲教授,成为国际乐坛上第一位获得美国终身教授职位的华裔作曲家。
多元化的女性创作不仅是女性音乐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音乐发展的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单一的音乐语言表达方式,并在与性别冲突与调整中变得更加深刻。如今,这些女性以作曲为职业,其体裁广泛、风格各异,包含大量以往被视为属于男性的音乐形式和风格特点的音乐作品。她们已经走出闺秀派的风格,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女性作曲家的魅力。不仅如此,她们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频繁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并在主要的专业音乐院校担任或客串音乐教学工作,树立了牢固的专业和社会地位,体现出其在改革开放后的蜕变和多元化走向。
四、小结
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大都和社会变革时期的各种运动紧密相连,使得创作主流的话语模式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女性作曲家受其影响颇深,其音乐创作更强调对社会忧患的认识,而非个人女性化的表达。在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的性别观被官方所推崇,女性意识再次在宏大的国家、民族背景中被掩盖。女性作曲家也与男性一样,自觉关注社会、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表达。
政治、战争等宏大题材历来由男性创作,女性参与革命本身即是女性解放的重要标志。新时期女作曲家的社会参与意识更为自觉和主动,她们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投身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浪潮,实现了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转换。虽然由于出身经历、教育背景等原因,革命时期的女作曲家在创作上尚欠功力,但相对于中国古代女性音乐家,她们的视野更加开阔、题材选择也更为广泛。因此,她们的创作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观念的继承,不但意味着对传统闺阁文化、青楼文化的超越,更是通过对纤弱卑微女性角色的反叛,从而促成了中国女性的历史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