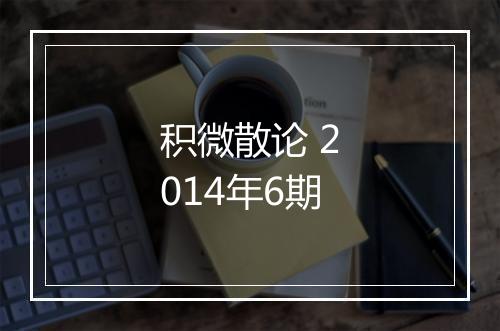积微散论 2014年6期
胸怀
伊姆莱的话言简意赅:生活,反正不是抗议,就是合作。
一辈子只会抗议的人,会很无聊。还不如选择一次战斗。一辈子只会合作的人,会很平庸。现实生活中,抗议的成本太大,所以一般情形下诸多的合作其实是无可奈何的。
为了合作的抗议也许是清醒的。允许别人赞美我的对手,我们同在生命场景里,都有着相同的权利。
胸怀不只是说说而已,它需要在实际生活里生根并检验。做一只无限大的容器,一切都可仿佛,原则的方向自可不改变。一只苍蝇不能把我们气死,我们的容器里有现成的苍蝇拍。有胸怀的文字总能对别人有点用处。
世风日下或人心不古?做一个经常扩扩胸的人。 山谷
我一定会进山的,但只是偶尔。
说到进山,因为我想让我所待的地方和自己一道沉静。我从未想到躲避灰尘或远离人迹,因为即使身处山谷,我热爱无比的山谷,看那里的一年四季,看石头和树木,看山谷上方的阳光、天空、云、不知叫什么名字的鸟,认真地看。同时认真的是继续想山外的事。在山外时放不下或过于快速反应的行为,放在山谷回味并加以反思。
山谷给了我太多的启示。近四年,在北方的某一山谷,写过《我们(二)》《有理想的人》《我是山谷》《高地阳光》《老佛爷山》等。山谷让我们必须包容,山谷让我们同时懂得以向下的深度去表达另一种高度,山谷最大的提醒是山泉流出山谷,流进外边广大的田野,山谷也不全是洁身自好地静修,它想去做些什么,起些作用。即使外边一片污浊或真的到了无力回天,它还有自己的山谷。
山谷里的感受我尽量在自己的创作中应用。文字亦可以向下的深度去实现高度,向下,与身外关联,与世人关联;而包容与起作用恰是写作者素质和作品效果的佐证。
最近,山谷去得少了。
它的形和质在我的心里。每个人在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山谷。 忍耐和“装孙子”
你看,人类原本从一开始就该一切美好,但每个人都在活着时忍耐了一生。
冲冠一怒为红颜或轻易地拔刀相见,后果往往会失控。麻烦已经有许多,失控的局面会妨碍我们保持简单。散文诗不是檄文,不是咆哮,不是怒不可遏。(前两年,我的《圆明园》《不怕鬼》《深夜,突起的心思》就有忍耐不够之处,把剑亮得过于迅速。)
我扫了你一眼,我递给你一支烟。我岔开话题,讲秦桧,讲魏忠贤,他们都令人愤怒过,他们让许多人不仅忍耐,而且还要“装孙子”。历史中最后成为“孙子”的是他们。让令我们暂时选择忍耐的人和事自己慢慢变化,慢慢露出破绽。
写作中,忍耐是痛苦的。忍耐是为热爱,为了不放弃信念。实际生活中,我不赞成去“装孙子”,卑躬屈膝会使文字失去光泽和品质,会让文章趴下来,更会让写作者自己没有了脊梁。
忍耐,我们自己和世界都有了一个过渡。
过渡――变化与结果。 浪漫
我呼唤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拒绝追求的方向,只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人、事物的关系。没有具体的后遗症,只是精神的特质。如果非要走近,像走进大自然一样,像摇晃装着小半杯红酒的酒杯,像在咖啡吧的某张桌子旁坐下,闻着咖啡豆的香。我反对以浪漫的名义去浪漫,但同情生活中那些伪君子,满口道德文章,却于事无补。 文字本身与文字背后
写作是个苦差事,它六亲不认。你是王侯将相或富可敌国,若想拿文章来说事,文字本身的功夫和文字背后的意义就不能僭越。
文字本身得像个文字,就像画面本身得是个画面,作家和画家的基本功早已为人所认同。
吸引、把玩、惊叹到珍藏,收藏家有心得。
散文诗文字本身的受重视,已经很久了。正的,倒的;里的,外的;远的,近的。文字的功夫用得不可谓不足。我们言必提到的一些名家,之所以作品为人传诵,其实更多的是文字背后的意义。
很多人在生活中不愿站在背后,想领一些风骚,想活得光鲜,这没错。但没有支撑,文章掩卷,把什么留给读者?在花言巧语和真话真说、真话巧说之间,出于对生活的认识和经验,我早已摒弃了前者。真话真说或巧说,首先得发现真谛,而发现真谛得有付出,得有痛苦,否则,就会满脸真诚的样子,却说出了一大篇谎言。
眼前的景象足可以让我们眼花缭乱,眼见为实当然还不够实,还需放在历史经验里验一下,放在哲学里加工一下,放在我们自己的再三思考里磨一下。
不管我们怎样表演,人们想看到的还是我们在表演之外的重量、格局、高度和情感纯度。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叫着“芝麻开门吧”,门开了,里面却空空荡荡。我们失望吗?还是沿用经验式的安慰:我们的快乐在于行走本身。 泪水
唉,儿子现在已是个大小伙子了。他小时候我有两次对他动了手,都是和他因受委屈流泪有关。我告诉他,男人今后受委屈或遇到的困难还多呢,流泪是没有用的。眼泪是有尊严的情感,不能用它来为男人博得同情。其实,那时儿子尚小,我的理由多牵强附会,以致妻子到今天仍耿耿于怀。对不起,儿子。但我还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没为受过的委屈或失败流过泪,却常常因感动而流泪。多是独自一人,读到好的作品或在影院里的一个角落。比如去年重读弥尔顿的《失落园》,却为撒旦流泪;看《金陵十三钗》,十二个妓女为女学生去受难,当看到坊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被颠覆,我流泪;看《唐山大地震》,看到女儿喊母亲,为受误解的母爱流泪。我丝毫不掩饰自己有时孤独地看阳光和阳光下的事物,眼里会莫名其妙地湿润。
感动或被感动,泪水的意义在散文诗里或其他文体里都是特别重要的。我不赞成用泪水去表达人类的无助,提倡作品的目的地最好比泪水更远。流泪之后我们能想到什么,能做些什么。人类可以为喜悦、为感动、为真情、为温暖流泪,能否从此不为苦难? 诗人的心是敏感的,有的诗人动辄就会控制不住,其真情可贵,但将泪水流在无人处,我们会发现更有力量。 黑暗和过度诅咒
由于光不会拐弯,我们有时会站在阴影里。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觉得一些现象甚至本质让我们联想到了黑暗。叹喟或悲伤当属情理之中。歇斯底里式的诅咒说明我们ช自己在失去平衡,失去别人客观公正评定我们的条件。
我们的生命从黑暗中来,其实早已不惧怕黑暗,随便四处望望,大光明与太阳有关,小光明与萤火虫有关,当然,真正的永不熄灭的光源在我们的心里。散文诗文字的光亮,她的光源在写作者这里。多年多年以后,有两种叙述:
孩子,那时是多么黑暗,你瞧,我们不是走过来了吗?
孩子,那时是多么晴朗,你瞧,我们费尽心血,却走到了今天的黑暗。
我们不诅咒,不控诉。逻辑或抒情式地批判,用文字的力量去抗击甚至减少黑暗。 月亮
同是光明,阳光和月光是不同的。太阳本来就该在青天白日里出现,而月亮之光出现在黑夜,是白天留给人们的心有余悸的黑。太阳的光明有温度,而月亮的光明仿佛冰镇过,它收敛。弯月,光明苗条;圆月,光明丰满。阴晴圆缺又引起文人墨客和普遍人类的诸多联想,青春惆怅时,多梦多雨又和月色撩人有关。
咏月,静谧、柔美,任何年代诗歌作品里都不可或缺。
月没变,事在变,人在变。变了的人和事面对不变的月亮会说出怎样的新的话语?
从我个人讲,我在写作中如提及光明,我是希望光明不仅要寻常化,而且还要有温度。但因习惯彻夜枯坐,我不能对月色无动于衷。昨夜,一个人驾车停在京北郊的沙河水库边,仰头看月,皎洁的月,柔美宁静得让我心痛。再看眼前的水库,水面依稀有水鸟掠过,有蛙声,一阵风来,柳影婆娑。
爱、恨、情、愁,浪漫和现实,悲观和乐观,能拒绝这轮月,以及月下这一方意境?
只是,月亮是相同的,而“我的”月亮却必须只属于我。 角色与诗歌原点
谁能规定只有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写诗?谁又有这个权利?官员写诗有权力延展化嫌疑;商人写诗有资本推动嫌疑;曾经有影响的诗人,如今再写,又有黔驴技穷或强弩之末之相。
世界需要宽容,诗歌同样。入眼入心之作可以多读,可否不去讨论哪类人才有资格写诗?人间万象,仅凭一己之力,又怎能穷尽?各方面的人一定有各自独到的发现,你指着一棵山楂,让它结一树苹果,你正确还是它在受委屈?
回到诗歌这一原点,让作品本身发挥作用。作品之外的其他因素皆可视为谋生之必需。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的意思是让我们先安然地活着พ,其他身份皆是路的一种,无高无低,无贵无贱。
这些年,虽清醒意识到自身才华之局限,但仍坚持认真写作,想告诉别人,在近处或远方,我究竟看出了些什么。因为以散文诗的方式写多了,不免对散文诗的整体环境多加留心。所做的一些与个体写作无关的事,那也是尽一己之力而已。当然,我更希望无须尽这样的力,散文诗本身便能从容地发展,不左支右绌。未来会的?
你可以有权利爱,但不能强迫我接受。
事物自身在平静生长,过程简单或者困难,强赋之以愁或强赋之以爱,似乎都会不尽如人意。从根部还原事物与人的本质属性,舍弃拖泥带水的芜杂的关联,取其最本质之处来启发或感染。我们一生到过许多地方,我亦读过许多状景或行吟之作,发现不少作品里充满过多的爱。我上午爱着自己的小村庄,下午就去爱苏格兰的一个牧场,明天,我的爱又到了别处,冰岛或有企鹅的地方。爱是你的权利,牛羊对苏格兰牧场的感受你同时不能剥夺。同样,企鹅也想胸怀全世界,当那里的冰都化完了,人类的世界就意味着温情脉脉?
一旦过分自我,错误便开始。尊重他者,不仅是生活里的见识,更是一种哲学。
不是我给你转身或舒展双臂的空间,而是我自己就需要转身或者舒展双臂。人们可以失去自己,但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本质、自由、个性的丰富与世界的美好。勿强加于人或事,人啊,能有此胸怀或者觉悟? 被伤害,依然要平静
一个人爱过你,然后,她又伤害了你。你怎么办?你的态度很重要,因为它会决定你作品的品质。那种轻易就本能性地揭短式的叙述会让文字只能趴着或躺着。恐怕趴着或躺着的还不仅仅是文字。我们接受爱,更要学会忍耐被所爱的人造成的伤害。坚强是这样出现的。说到恨或者还击,我还是愿意把枪口对准那些敢于令众人民不聊生的人,对准那些抢我河山、辱我尊严的强盗。在做这样的决定前,光靠坚强不够,我们得有坚强的本钱,能同仇敌忾,能有“夷技”去抗衡。
因为知道有大恨,所以我们努力不能被“小仇恨”扰乱心神。曾经爱,如今只是不爱了。一想到有过的美好,我们不妨原谅一切。 归来者
艾青《归来者之歌》出版后,诗界把辍笔多年后又重新写作的人称卐为“归来者”。诗歌,一旦走进一个人的内心,就会不离不弃。无所谓去,又谈何归?因各种原因不写了,文字的诗歌可能变成了诗歌的注视,可能变成沉默的坚韧,也可以一声豪迈、一次叹息。更有人说,“归来者”因多年离开诗坛,对现在诗歌语境陌生了。经典的诗离开当下已千年了,我依然爱读。小技巧与大诗意,ง前者让人成匠,后者成师。匠人与大师,我们都需要。
一些整天与诗关联的人,不一定就与诗亲近,相反,诗歌很可能成为一种工具,更像面包机,或者烧饼锅。
诗歌,含有超然的能量,你如果没有经历超乎寻常的磨炼,是不能真正感受到诗歌的作用的。
比永垂不朽更为不朽的,是那个人留下了超越年代的诗的念想。 诗歌究竟有什么用
稍微读过书的人,就一定接触过诗歌。久远的诗歌文字,当下的诗歌文字,算是一种眼见为实。另一种眼见为实,恐怕与诗人本身关联。瞧,这个人他写诗。那些动辄就说诗歌没有用的人,其实又多是在说诗人在今天没有用。每听到此言,我和每一个写诗的人同样内心不平。但我不再争辩,多言无益,我写诗,这是我的一种活法,我从未说写诗能避免腐败不公,更不能解决钓鱼岛或其他问题。周围那么多令我们难受的事我都忍了,我写诗,你们为何就不能容忍?其实,没人能真的容不得我们写诗,我耕地不输于你,种庄稼或扛麻袋也照样行,劳动之余或夜深人静,我想些事,抒情或思考,我爱干这活儿,而且我并没有轻视不干这活计的人。事情就这般简单。说到“用”,更多的是关于权势或者财富。我必须不否认此二者确切有用,但如果否认除权势或财富之外其他一切也同样有用,会让更多的人绝望。所以,我坚定地认为,有用或者没用要看幸福来定夺。和有权又有财,一根白绫套颈,他生命的总结性发言不过如此。 几年前,因解决一件俗事,我办公室里来了几位青壮年。不请自坐后,将T恤脱下,我看到其前胸后背皆有大面积刺青,都是龙的形状。我笑了,他们问笑什么。我说你们的龙都在恋爱,它们的眼神多温柔,它们的爪子连指甲也没有,显然修剪过,更重要的是龙头都刺在你们心脏的部位,说明你们不是恶人,心里还有爱。为首的D开口了:哥们儿的话我们以前没听过,怎么听着像诗?我说,这些龙恋爱了,它们需要有点隐私。然后,他们把衣服又穿上了。再然后,都很心平气和。到今天,我心里着实喜欢他们的可爱和简单。偶尔,他们会送些茶叶来,说他们主要想听听和日常生活用语不一样的诗歌语言。
以诗歌的方式,江湖一笑泯恩仇。可以吗?
一位朋友,创业失败后,独自来到海边。我怀疑他原本想一直向大海深处走,把自己从此走没了。接到他的信息后,我将十年前写的一章《男人》发给了他,并让他就近找一块石头坐下来,看看海,再听一听。后来收到的信息是:“平生第一次,我感到大海的大没有让我小下去,而是让我竟然可以和大海一样大。人,到一无所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切可以有。”唉,其他方式都不管用的时候,也许,就是诗歌显身手的时候。
1995年,当我决定留在北京时,我一个人从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向东走,走到天安门广场,直走到两边建筑物的窗子都亮起了灯。看看那些窗子,当时我异常伤感。城市庞大,而没有一扇窗子是我的,没有一窗灯火是为我而亮的。
露宿街头又能怎样?我那天的结论是:没事,我需要的不是这些窗子,我需要的是整个天空。 诗歌有用否?
为了生计,我必须把一块空地说成是有形的房屋,并形成租约。一位行长带人看后,问:什么都没有?你把阳光和空气租给我们?恰巧,一群鸽子从头顶飞过,我说,不是,租给你们的除☂了阳光和空气,还有一群鸽子。
后来,那单事做成了。
太性情,成为我自身的短板。我因此不会成为一般意义上成功的企业家,亦无此愿望。当别人将我与周遭环境比较性评论时,我便常常拿读书写作来自我安慰。更大的安慰是每当遇到不如意或失败时,古诗里一些励志的句子就会冒出来。不气馁,不是因为我坚强,而是气馁了情况只会更糟。因此,在看上去无助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咬紧牙关,坚定地说出热爱”。说到无助,失败时会,成功时亦会。无助的表现形式非常多,不仅与功名利禄有关,更与精神有关。诗歌,可以让我们从容地走出抑郁,但也会让我们从此走向抑郁。
感谢诗歌,她让我对天敬畏,而对人或事我可以无限忍耐,但绝不妄自菲薄,亦不会为利益而自折其腰。
可以是有,为什么就不可以是无?
中间的许多细节,我暂以诗的方式予以删除。 天涯和海角
你到哪儿都甩不了我,或者你到哪儿我都心甘情愿跟随,即使是流浪,也要在一起。知道这不过是个比喻。创造一个无尽之远,表达愿望或决心,传统的爱情诗里常见。事实上,天无涯,海亦无角。海南岛曾是古代流放之地,像沙俄时的西伯利亚。在三亚的西南,真有几块大礁石,一边就真的写着“天涯”,另一边写着“海角”,两处相距不过百米。到了那里,你执恋人之手,从天涯走到海角,一百米就走完了。
天涯海角之远在我们真实生活中又是必须的。近处烦你够呛,闭上双目就有了远方。人迹稀少,最好只有自己,无人盯梢,无人与你争权夺利,至于朋党之争或诸侯各怀鬼胎,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把自己彻底远开去,原来的近处所存在的各种烦恼反而仿佛黄粱一梦。
问题是,有再远的远方,最后,我们还得回来。
回到日益同质化的城市,回到小镇或村庄,你闻油菜花,也得闻牛粪;你看灯红酒绿,也得看城市的生冷坚硬与嘈杂拥挤。至于更多的你不愿看到的景像,如灰尘、如潜规则、如垄断等等,你恐怕都得看。有的,你如不认真严肃地看,还很难一下子看得出来。
就是这么一个近处,你愿意回来吗?
实际上,是你根本无法真正走开。天涯和海角与咫尺近处,有散文,有诗,有故事,还有杂文。怎样的体裁无关紧要,问题在于即便你有了远方,这近处你还要不要?文字里的近处是大家都熟悉的日常场景吗?
你看,眼前我们总是忧心忡忡,最起码喜忧参半。如决心太远或干脆逃离,你个人可能清静了,人间的事又岂能与我们无关? 清谈
两种描述方式:
1.就自身之外的各式话题,有针对性或信口开河;在当下众人大多忙于自身活计的情形下,能清谈一下,总算良心未泯。可能提出很多方案,参加谈的人又都无力予以实施,所以只能清谈。文人的清谈古即有之,当局开明,可百花齐放;如当局量窄或短处过多,清谈没准还会获罪。
2.所以这第二种关于清谈的描述往往让清谈者不快:站着说话不腰痛。除了说些废话,干不了一件正经事。
民间议事往往体现自发的良知,匹夫有责是从这里边生长的,书生报国亦是。谈偏了,或谈错了,因为谈的人大多无能力进行实践,因此一般不会铸成实际效果的大错。
然而,在读各种诗歌作品时,我希望读到的是一箭中的的发现,读到人性该有的温度,读到人类一直困难重重但直到今天仍在生生不息。
何谓站着说话?难道站着就不能说话?
土地干旱时,需要雨。闪电或雷声,它们本身不是雨,但它们是下雨、下大雨的有机组成部分。
闪电、雷声、雨,与随后的禾苗茁壮是散文诗的系统工程。从闪电,我们看到了乌云里的光明;从雷声,我们需要振聋发聩;从雨,我们意识到人间可以不干燥,可以不起灰尘。而禾苗生长,更加关系到我们能否活下去。 观天,但不坐井
坐井观天,是不能让我们德高望重的。我带着我的爱好活着,无其他奢求。我的爱好更多的是与散文诗有关,仅此而已。非欲借此去博得功名,至于利禄,更属可笑。我心底倒真的希望写好文章的人能从此不愁功名利禄,从此告别落魄。 正因如此,我觉得有权看整个天空,而非一井之天空。天底下比我优秀的人多了去了,所以学习,所以交流。散文诗向其他文体学习,亦说明它本身就是整个天空底下的事物,而非偏安一隅,更不是那个赵构治下的南宋小朝廷。
不坐井观天,就像不满足于拿一杆单筒望远镜,以为远方只是远远的一个圆。世界之大,都在圆外。再说学习,有些文友担心怕把散文诗学习没了。中国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不是还在吗?我们向李白学,既没变成李白,也没把我们学丢了。所以,无企图地生长反而会令散文诗焕然一新,从容存在。
密斯在格罗庇乌斯之后,就现代建筑提出了著名的“少即是多”论说。
少,为什么就能成为多?设计师或写作者心里首先要有多,没有整条龙,何处去点睛?
拒绝复杂与烦琐,首先是因为我们对复杂和烦琐已有足够的体会,我们的生命已难以承受太多的复杂,一些力量就是整天地支弄你,你想简单,他们不让,因为他们想简单,所以复杂的苦痛只能落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
没事,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体会一切。
慢慢地,我们也能一针见血或语重心长。没用的话留给风去吹,我们面对一扇窗,却也可以拥有一片江山。位高权重又能怎样?盘下整个山河,最终也只是看看,看上一辈子也只是看看。
所以,我更喜欢明代的木器,比起清代的烦琐复杂,明代的匠人更显得简洁入骨。
文章的简洁,它需要有深处的意味。因而,入骨则体现写作者的功力。这种功力往往在诗外。 海浪
近读英国女作家伍尔芙的《海浪》,她是当作小说来写的。其实更像大章散文诗。时间、地点、人物、情节、意义等诗统元素皆被颠覆。人生需要设计,但更是不可设计。世上如果有什么不能按照规划来展开,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极像海浪。一道浪,又一道浪。浪到了海滩,浪继续涌来。被浪画满的水面一望无际,就成了大海,大海就成了我们的生活模样。
对海浪的过分重视会让我们误判大海的实际情形。跳开此话题,谈到不久前我与一年轻诗人见面时,他说: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后面的浪把前边的浪推到沙滩上。他不相信往事。
他把海浪说到别处。浪就是浪,前边的和后面的都是海浪。你推别人,或别人再推你,不是我们评定别人或自身生命价值的好的比喻。前边的浪是往事,后边的是未来。否定往事的人,你这一浪也会被否定。
海浪多了,像满脸皱纹。原本平静的大海,不由分说地起了波澜。我们长满皱纹的脸庞,内心亦满是沧桑。理想、爱情、价值、自由等大词汇,有的沉在海底;有的邈远成点点帆影;有的像海鸟,飞来一下,又倏忽飞走。
生活的故事有时不需要主题,一浪又一浪地律动。但我们不能忘却大海深处,不能以为海浪就是大海的全部。 浪漫主义
30年前,在大学读欧美文学,总碰到浪漫主义诗人之说。像雪莱、拜伦、海涅、普希金、歌德等。诗人,倘不浪漫,就会被淹没在现实中,窒息或沉沦。这里的浪漫,是指对现实的一种能动,是超越和努力在现实之上获取另外方式的精神图腾。但冠以浪漫主义,总觉得有些别扭。什么事,一旦成为主义,就意味着找根绳子把自己捆起来。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他若想纵火浪漫,得先从绳索里解脱出来。
嫩芽一旦出土,就会向空中浪漫。如果是果树,它会浪漫成花,浪漫成果实的甘甜和芳香。但它的根本是土地的现实存在。用一种风格去圈定一个诗人,往往忽视诗人的复合性,忽视诗人对土地现实的需要。他以浪漫的调调,给予桎梏我们生命的现实环境一些超然,一些豪迈,一些飞的感觉和永不绝望的抒情。
今天不好,明天更好;或者,明天局势可能更严重,所以,今天就很不错了。浪漫主义也许就这么简单。它一定基于现实,欲改变或实现。可能是浪漫现实主义,可能是浪漫象征主义,也可能是浪漫表现主义。这么说有些不严肃,然而绷着脸说出的不一定是真理,那像是政治报告。
现实尽收眼底,浪漫些,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恩赐。别人冷落我们,我们自己身心荡漾。灵魂飞扬,在天空里。那儿没有联防队员,没有欲盖弥彰,无须暂居证,心绪可以自由自在。
假如被浪漫主义了,你一定不能从此瞧不上现实。因为还有另一种力量――现实主义。 家
所谓男儿四海为家,甚或地球就是我的家,那皆是大话。
不要挽留我,以爱或以恨。不要挽留我,以一个情节或一片风景。我要回家。
家,就是这样。我是自己的主人,我想蓬头垢面,想把脚跷在茶几上,把书一本一本地翻,然后扔得到处都是。我是自己的主人。
散文诗,太需要回家。它有自己的家。它被散文挽留,被小说挽留,被情书挽留,可以略作停顿,然后让它回家。
巢,就在屋后,几只喜鹊在飞。如果是五月,槐花会香。 上中下
事物的基本结构,更像社会的实际图景。下,最为有形,最广泛的群体每天的现实存在,所见或所想,小喜悦或大叹息,都取决于基础部位好的与不足的之间的比例关系。我们的笔极易从底部开始书写。民间或底层状况,尽管最大的事都是最必需的事,但被忽视或者干脆以过于普通而推诿,势必会引发人们小喜悦的失去,大叹息的增多。2009年,我曾写过《英雄》,是把平凡者看为英雄,他们本都是英雄的子民,大英雄的名字容易被历史镌刻,小英雄依旧平实着,大小英雄在历史上曾互相转化。一般情形下,小英雄们把公共的义务以契约方式签出,为的是换取幸福和尊严。这是个底线,任何人都不会把此权力签出去。2010年写过一章《沉默的砖头》也是从上层建筑的对面看基础的“砖头”形态的存在,亦是关乎“下”。农民工进城引发大量的“底层写作”。甘苦和复杂,我想读到坚韧的精神、不屈的精神,和最广泛的具有决定性的社会的意志。但不能忽视另一个极端,似乎不写“下”就是缺少普世良知。整个板块是个系统的问题,上中下都协调了,问题才会减少,希望才会变多。“中”的力量表面上在增强,但最被漠视的恰恰在于此。“中”,自立的能力强些,忽视它理由似乎很充分。一株植物,中部很少出故障,要么根部溃烂或根须干脆罢工,要么顶部枯萎或花谢叶落。一个事物,倘上下出了问题,便是整体问题。可是一提及“上”,常讳莫如深。对高高在上的东西,我们常看得模糊。身体各部件都好,精神系统有了问题,这一定是个大问题。 声音从四处传来,我向哪里凝望?如果有了方向,我们能否望得更远?所以我不断想到灰尘,这个意象我是如此不喜欢,但又必须每天面对。当我们列队经过时,有风起尘,事物不像从前纯净,但我们确实又在进一步行走。尘埃,你惹与不惹,它在空中弥散,一场怎样的雨,才能洗净天空?如果雨迟迟不来,我们的目光就从此不能看得更远?
未必。
心中有纯净,污垢也从容。你可能深陷污泥,我宁愿在尘埃中走远。
上层建筑的重量,不全是泰山压顶,鸟有翅膀,在山顶上飞,我们可以攀登,站在山顶。
孔子在未落魄时,说:登泰山而小天下。
你在高处,看芸芸众生如同蚂蚁;你在高处,同时也会小成蜜蜂或小成苍蝇。这取决于下面的人怎么看你。
想起堂・吉诃德
血液里似乎有本能的冲动,面对一些缺憾,哪怕与自己无关,都会有斗争的冲动。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冲动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
在北大时,未名湖畔有座塞万提斯像,常一个人在那里坐会儿。堂・吉诃德是个理想主义的圣斗士。我在2009年写过一章散文诗,写的时候有莫名其妙的悲伤。把长矛刺向空中,谁能记住空气中刹那间的伤痕?问题是,敌人是谁?他们在哪里?唯一让堂・吉诃德欣慰的是:敌人自己在倒下,一个接着一个。倒行逆施或粗暴无道,或贪污腐败,他们自己在倒下。当然还会再生,像割了一茬韭菜,又会长出新的。
堂・吉诃德可以选择不斗争,他可以走向一个人的浪漫,但他手里的鲜花还未献出,已经有了一大批情敌。堂・吉诃德绝望否?
世界上,绝对的势均力敌是不常见的。我们与很多有来头的力量不可能对等。要不要亮剑?要不要证明自己的气节?
日常工作中,常遇到一些派头十足的主,以祈使句的口气让我们无法自由选择。我说,你有能力让我们活得悲惨,我已经看出你的能耐。而且我还希望看到你更大的能耐,比如,一些国家,大的或小的,在欺侮我们,你去把他们灭了。或者,你把你的单位的旗子换成五星红旗。说到五星红旗,如果再听一下《国歌》,我不仅行注目礼,而且还会热血沸腾。
堂・吉诃德的这种看上去不自量力的精神,也许更是诗歌的精神。
比如此刻,凌晨四点,在书房的灯光下。室外,纺织娘不间断地鸣叫。
好长时间我是坐着,满脑是亨利・米勒《巨大的子宫》一书里的影像。
世界正被一点点地装进一只口袋,谁是谁的乾坤?谁是口袋的制造者?谁是口袋的主人?即使装得下,所有物件拥挤在同一袋子里,怎能有好的感觉?我的肉体只是件简单的容器,里面除了灵魂,皆属空空荡荡。
肉体与这个世界怎样关联过,时间知道,灵魂知道。还有,那些被关联过的人与事,知道。 红处方、处方、非处方
人有病,天知否?凡生灵哪能无病?只是人类的病更被人类自身所关注。病因很多,病症亦杂,身体之病像寻常事件,自不必太显惊奇。看看社会,精神患疾,何药可医?
为防毒性的副作用,为避免嗜毒成瘾,医者开的最谨慎的处方叫“红处方”,女作家毕淑敏写过一部同名小说。革命,曾是历史的“红处方”,当不能擅用,改良,是历史的常规处方,而社会的保养和保健,竟然靠我们自觉地重现“非处方”。
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开出怎样的处方?谁开?谁用?有病的给没病的开?那些药是否真的有效,会不会没病吃出病来?
阅读的时候,想寻找答案。写作的时候,想给出答案。一不小心,就会越来越痛苦。最终,会陷入绝境:我们谁是谁的病人?
对于平凡者,忍耐是最好的处方。忍耐之外,看看周围丰富的一草一木,它们也认真地注视我们。慢慢地,它们成为我们的非处方药。女诗人爱斐儿的《非处方用药》我又认真地读了一遍。她动员草木为我们治病疗伤。被漠视或误会,不要紧,它们以默默生存的方式等待被发现。除了它们能起到一些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希望我们能同时发现它们内在的情感。人类的精神正在枯萎,草木的关心反而更加自觉。我们有愧否?
有一天,救你的是一根枯藤,而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名字。
无数不知名字的枯藤,一起救救我们这个世界? 误会
一条路走下来,所有的误会都留在了身后。就你见到的和经历的,不谈你对诸多事物的爱和感受,那些事物无一不热爱你,它们不论高矮胖瘦,都希望被你留意和爱恋。
但你得行走,有些爱可能你会说出来,有些迷恋极有可能沉默在心,许多时候,轻声叹息,然后继续走。
有多少误会由此产生?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没有停顿,不是冷漠或者绝情,只是你如此喜爱金黄的麦田,但麦田不能与你一起走,你感谢蒲草或芦苇邈远了生命的局促,但你无法带着它们前往下一个驿站;你为一朵莲花流下了泪,但你行将赶往的地方是沙漠,你可以爱莲花,但又不能带着它变成大漠上的枯萎;你继续行走,经过村庄,经过都市,经过森林和河流,你心里知道,你爱它们,但你继续行走。
相对于爱就要厮守,你的行走意味着一次又一次告别和远逝。它们说,你的爱永远只是远方?
丰富的事物,不厮守的爱如何表达?心头日益沉重,误会甚至怨艾越来越多,你就此停顿?
你的身影渐渐远去,误会或者爱恋,它们或留在身后,或凝成形而上的意念。
想想一缕风、一抹夕照或一泓溪水,它们对人间万物都是热爱呢,你走远,渐渐地也会成为一缕风、一抹夕照或一泓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