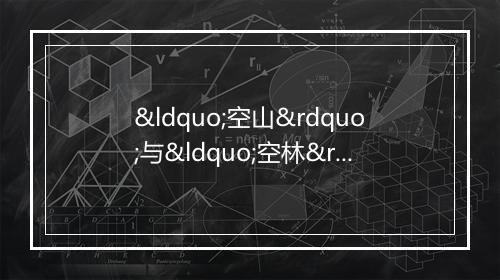“空山”与“空林”
摘 要:阿来的《空山》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两部小说,都描绘了边缘少数民族地区在外来文化力量的强势入侵下,发生的断裂性的彻底改变。本文从现实环境的破坏、传统文化习俗的失落以及神性与人性的双重消弭等方面入手,讨论这些古老村落、部落的固有秩序所受到的毁灭性打击。小说里的村落与部落,作为众多村庄的缩影,其遭遇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
关键词:《空山》 《额尔古纳河右岸》 边缘 毁灭
藏族作家阿来的《空山》和黑龙江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描绘了少数民族边缘地区村落、部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与迁徙,表现了他们在外界的强势入侵下逐渐瓦解、消亡的习俗与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生活环境遭到破坏,传统的民族文化遭到入侵和毁灭性的打击,其固有的“神性”与人性也随之消散。
阿来在《空山》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名叫“机村”的藏族小村落在现代社会强势话语入主过程中的歌哭悲欢。空山之“空”,既是天火肆虐后洗劫一空的那座荒山,也是遭遇现代社会与政治冲击后的传统文化的失落,抑或是那个激情澎湃而又虚脱的时代下神性的解体与人性美好的遗失;而《额尔古纳河右岸》用平静的笔调,以九十多岁“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的口吻讲述了鄂温克民族的世纪变迁,同样表现了这个原始而传统的族群在面对现代文化入侵时的被动与无力抵抗的尴尬与悲哀。
一、“刀”与“火”:环境的破坏
《空山》讲述了无休止的砍伐毁灭了山上屹立了千年的树木,一场从天而降的大火吞噬了山上所有的生灵,造就了现实意义上的“空山”。在那个时代,砍伐树木的名目有很多。从那时起,“除了千年大树轰然倒地的声音,村子里就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
随即而来的一场天火,在始终抓不住重点的“救火”行动中变得势不可挡,席卷了这座山的一切生灵:桦树,山花草丛,飞鸟走兽……一座空旷的山,是对于“空山”最直接的解释。机村人不明白,祖祖辈辈依傍着的山野与森林,怎么一夜之间就有了主人?悲哀的是,他们只能听命,无计可施;而随即发生在那个躁动的时代的一场天火肆虐,成为造成“空山之空”的致命性因素。
位于中国最北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也经历了类似的浩劫。1957年,开发大兴安岭的号角吹响,新中国的林业工人大量进驻山林砍伐树木,目的则是投入新社会的建设。思想简单又淳朴的鄂温克人“既要当他们的向导,又要用驯鹿帮他们驮运帐篷等物品”。于是,一颗又一颗粗壮的松树被装在运输汽车上,运到山外去。1965年的冬天,国家开始了对大兴安岭的大规模开发,“更多的林业工人进驻山里”,“伐木声也越来越响了”。最可怕的是,大量的砍伐给这片森林带来了重大的灾难―― 一场大火。两个林业工人吸烟时乱扔烟头,森林迅速成为一片火海。这个族群只能以最后一位萨满的生命为代价,才熄灭了这场大火。
纵观历史,1949年以后的中国,随着对边疆地区(主要是东北大兴安岭一带的森林)开发的大力推进,对林区生产实行了国有化管理。在“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事业”的伟大名目下,大量的天然森林惨遭无节制的砍伐。陷入疯狂的人们没有想到,过度砍伐的后果就是:短短30年间,“生产木材就达6亿多立方米”,“用大火车装载,节节排列,那么可以从中国黑龙江最北端的漠河到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近三个来回!”{1}
建国以后,边远的少数民族被纳入民族统一的管理之下,他们世代所依赖、热爱并敬畏着的环境遭到了政治之“刀”与疯狂之“火”的肆意践踏。事实上,《空山》中机村的人们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描写的鄂温克人只是千千万万处于边缘地域民族的缩影。可想而知,随着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所承袭的古老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将不复存在。
二、传统的失落
《空山》的副题是“机村传说”。在藏语里,“机村”是“根”的意思,“机村传说”也就是关于“根”或“源头”的传说。根又可以理解为机村人的信仰与传统,因为没有了这些,机村也就不复存在。作者阿来将充满悲悯气息的“空”与副标题中的“根”字并列来命名这部作品,是有深意的。作为一个“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混血儿”,作者在用汉语抒写藏族文化的同时,“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2}。我们很容易发现阿来想要在作品中回溯藏族文化,还原精神家园的愿望。然而,面对象征着藏族文化的机村,阿来却只能唱出一支支对于曾有文明的沧桑变迁的挽歌。
1.打破固有秩序 新政权建立后,一夜之间,村子周围设了许多关卡,机村人第一次感受到政权交替带来的变化――给他们的行动带来了禁锢。接下来,变化表现在劳作方式上。土地变为国有,村民们必须通过集体劳动获取生活必备的食物:“(机村人)被沉重的劳动压弯了腰杆,一天劳碌下来,只是由别人舔着笔尖,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几个工分。”
在生活习俗上,“烧荒”事件是最好的体现。国家收回了机村的土地和边上的山,禁止机村人进行千百年来相传的“烧荒”――因为这是在“破坏国家的财产”。机村人不忍心看到牛羊无草可吃,只能冒险烧荒,领头的巫师多吉却一次又一次被“带走”“谈话”。
突然之间,机村的人变成了自己“主人”,然而,这些“主人”们却必须放弃自己原来的观念和生活习惯――他们再不能对祖祖辈辈生息其间的森林与草地进行独自地处理了。“所有制”的更替,将原先从属于村庄共同体的范围内的所有物产全部收归“国有”,改变了机村长久以来固有的生活秩序。
2.遗失宗教信仰 在对待死亡的方式上,信仰的失落已有所体现。藏族人重视灵魂,他们相信“天葬”是一个人用躯体对这个世界最后一次的施舍。这种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的信仰与传统在新社会遭到了意料之中的反对。汉地的土葬方式传来,天葬被取代。在这关于死后遗体与灵魂归属的争论中,机村人败下阵来,只得被迫改变千百年来的信仰与习俗。
小说第二部分《天火》,则更加直接地揭示了机村人的精神家园,在面对外族制度和思想侵入时所引发的冲突和矛盾时,机村人世世代代所信仰并奉为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灵被毫不犹豫地推翻并被打上“落后文化”的印记。机村人只是心痛地看着佛寺被拆、金妆神像被毁,然后大哭一场,“假装忘记”这些“旧神”,接受现在的生活。 天火烧起来后,手足无措的领导在勘察后急忙做出决定:炸掉“机村的风水湖、所有森林的命湖”――色嫫措。“这湖没有了,这些森林的生命也就没有了”,但机村人却无力阻止。于是,色嫫措被炸出大洞,形成一个大漩涡,吸进所有的湖水――这无疑是机村世代信仰的风物的反抗,是对于人们信仰背叛的惩罚。
“就算天上真有神灵,也移座到别的土地与人民头顶的天空中去了。”这大概就是古老信仰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所陷入的尴尬。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机村人心中视作生命的深深扎根的信仰就这样轻易被无情地否定了,只留下生疼的冷酷记忆和经久难以愈合的创伤。
与此同时,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也以类似的笔法书写出了处于边缘地域的民族连带他们的文化在强大的主流文化面前无力抵抗,只能成为弱者,从而被同化、被吞噬的残酷现实。
小说开头,叙述者自称是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这在一开始便暗示了鄂温克民族与鄂温克文化行将消亡,或已然不复存在的事实。
除了最后一个酋长,作者还用大量的笔墨向我们描述了最后的两个萨满。“萨满往往被认为是神和人之间‘互渗的媒介’。”{3}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描述了萨满的神奇力量及其在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通过萨满跳神这一最基本的宗教仪式,可以达到祈福、祭祀,为患者治病、为死者祝福等效果,她塑造的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作为鄂温克人的精神领袖,贯穿了整部小说。然而,最后一个萨满――妮浩萨满却在一场人为引起的大火中跳神求雨而亡。“在萨满教衰退过程中,政治、经济因素的介入以及外来文化的传播等各种因素在起作用。”{4}大量的砍伐和对森林环境的破坏迫使原始的居民离开原本的住处,从此他们的生活中不会再有“萨满”,这古老幽远的精神信仰只能存在于愈渐老去的鄂温克人的记忆中,并随着萨满的消失而消逝。
“没有一个民族会因为发展现代化而失去传统,发展只会使自己的传统文化更加发扬光大。”{5}阿来非常厌烦“越是民族就越是世界的”这样一种观点,“强势文化以自己的方式想要突破弱势文化的时候,它便对你实行鸵鸟政策,用一种蚌壳的方式对你说:不。”{6}
而机村在被强行灌入强势文化后,最终以一场史无前例的天火表达了排斥与反抗。在强势文化的倾轧下,机村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这场大火中逐渐萎缩。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人的遭遇又何尝不是这样?与机村所不同的是,鄂温克人以沉默的顺从哀悼着ツ他们的现实与精神家园。除了叙述者―― 一个九十多岁高龄的女人和一个愚痴的孩子,其他人都搬下山去住了。然而,他们的坚守在一定程度上是无力的,象征着民族文化、信仰的风烛残年,更添一种苍凉。
最终,阿来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变更,包括他在内的世世代代的藏族人心中的传统文化与信仰已经面目全非;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呈现给我们的,也只是一曲哀婉沉痛的文化挽歌。
三、“人定胜天”¿:神性与人性的消弭
《空山》向我们讲述了两个有关“谎言ฑ”的故事:《随风飘散》写的是村落中的谎言,善良的少年格拉在机村的谎言中忧伤而死;《天火》写的则是有关意识形态的谎言,青年索波在意识形态的翻云覆雨中茫然迷乱,机村的人性在一场大火中被荡涤干净。
《随风飘散》中被一颗鞭炮夺去性命的兔子,可以看作是机村“神性”的象征。他一出生便身体孱弱,当全村人都诬陷格拉时,他一遍又一遍地为他辩护。在机村,唯独兔子的内心澄澈透明,依然心存慈悲――所以在那个年代,兔子的生命力才会这样脆弱,一颗小小的鞭炮便夺去了他的性命。这里我们可以认为,兔子的死亡,寓意着机村世代信奉着的神的远去、解体。
第二部分《天火》,描写神性在机村的渐行渐远。在这场天火中,机村人被迫砍伐世代奉为“神树林”的那片白桦林,炸掉保佑“机村的风水湖”色嫫措……这些,都是神性在机村持续解体的表现。时代的变革与外来者的进入,使机村延续千百年的神性面临骤然解体的同时,机村原本淳朴的生命和灵魂也发生了改变。
《随风飘散》中,机村这个原本友善好客的村庄,因为桑丹、格拉母子来历不明的身份以及格拉是“私生子”的事实,村民们一直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并对格拉母子施暴,逼走他们;兔子被一颗鞭炮炸伤,几乎机村所有人都说是格拉炸伤的。对于这个从小得不到父母疼爱的“私生子”,除了心存神性的兔子,其他机村人表现出的都是残忍、冷酷。
第二部分《天火》更是将机村人性的遗失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从天而降的火,不但烧毁森林、烧死动物,更烧毁了机村村民人性中美好的部分。救火的过程中,机村人开始了无休止的偷窃,“几天下来,屋里的馒头干已经快码成一堵墙了”,连救火女英雄的母亲也将医院的痰盂偷回家成为盛放酸奶的专用器皿了。
大火是可怕的,但在大火中灼伤了的人性是更加可怕的。一场大火,烧掉了机村虚脱的表面,其包裹着的神性与人性的美好早已不知在何时遗失,对于一个视信仰如生命的封闭而淳朴的小乡村,神性的解体与人性的遗失无异于是这个村庄的消亡。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神性的解体与人性美的遗失是比较隐晦的,集中体现在萨满及其仪式的失落上。
小说中所描写的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是神性和世俗性的双重代表。一方面,萨满是深入到族群每个成员心中的神,有着无比神圣、强大的法力。“充任萨满的人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充盈着,肩负着沟通神界与人界关系的使命,神衣神帽披挂在身,手执神鼓,便进入到一种不能自已的迷醉癫狂状态。”{7}通过“跳神”这一仪式,能祛灾祈福,能使久旱下甘霖,能使病人康复,也能使“黄灾”(瘟疫) 消退。“萨满”的神秘性使氏族成员形成了一定的敬畏之感,而跳神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鄂温克族人为了民族而牺牲自我的高贵人格,这种纯洁无私使萨满成为真正的鄂温克族人的“人格神”,具有人性之美;与此同时,萨满身上的世俗性又能让游猎的生民们感到亲近――他们从自己身边的人中间产生。在萨满的身上,可以看到神性和世俗性的同时存在,这与藏传佛教中的“活佛”极其相似。 与此同时,《额尔古纳河右岸》也刻画出了其他鄂温克人思想品格的淳朴真实,他们热情好客,无私地帮助他人,即使是对小偷也给予了不求回报的帮助。然而,随着最后一个萨满――妮浩萨满的倒下,以及鄂温克族人的分崩离析,鄂温克人的历史中不会再有“萨满”,他们群居、打猎、迁徙的生活方式也将不复存在。可想而知,在那些下山住在楼房、过着现代生活的族人们心中,“萨满”将会变成一段逐渐泛黄的记忆,而那些与游牧生活紧密相连的生活记忆、鄂温克人对生活和对他人的热情、他们人性中的自然与美好,也将随着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变迁而渐行渐远,最终消逝。
四、结论
机村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民族,只是一个符号性的存在,却代表了一种普遍性的命运。从这两段遥远的传说,看着久经沧桑的“空山”和饱受摧残的“空林”,我们不难联想到与此类似的许许多多的不知名的乡村的命运,它们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的传统文化与性格因素的命运。这应该也是阿来、迟子建希望通过作品,传达给现代人的启示。
{2} 阿来:《就这样日益丰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页。
{3}{4} 色音:《东北亚的萨满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第161页。
{5} 凌峰:《从〈尘埃落定〉到〈空山〉谈弱势文化命运的多样性》,《安徽师范大学宿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6} 阿来:《阿来文集・诗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7} 王艳荣:《关于民族历史的想象――论〈额尔古纳河右岸〉》,《名作欣赏》200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2]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3] 色音.东北亚的萨满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 徐权.神性与人性力量的直接交锋――阿来小说《空山》(机村传说壹)解读[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6(5).
[5] 王艳荣.关于民族历史的想象――论《额尔古纳河右岸》[J].名作欣赏,2009(4).
[6] 王春林,张玲玲.哀婉悲情的文化挽歌――评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J].名作欣赏,2009(2).
[7] 朱鸿召.东北森林状态报告[J].上海文学,2003(5).
[8] 陈廷一.林海雪原――东北森林资源现状的忧思和出路[J].国土资源,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