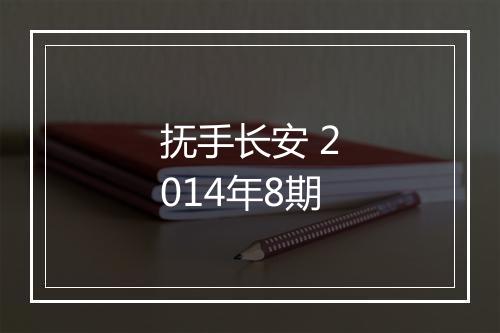抚手长安 2014年8期
一出车站,迎面便是斑驳的城墙盈满眼帘,来不及有任何的思想准备,身心便顿然消释在了汉唐。
遥襟俯畅,逸兴湍飞。多少世纪,多少风霜的矗立,在中原的腹地,阵阵西风自远古吹来,苍凉盈面。行走在街道,双眼恨不得将所有的景象,所有的历史一一揽入,已数不清到底有几个千年,几家王朝,几多天命轮转,几多悲欣交集。思绪随脚步缓缓而行,饕餮着春色初萌中21世纪的盛唐。
可以想见,一千年前,那个让中国永远骄傲的时代,在这里,究竟是一番何等的景象,大明宫大雁塔,曲江池,梨园管弦,花萼相辉是不必说的了。想当初,这里是李太白的青琐邀月,是金榜举子的走马观花,长安的街道,有来自波斯ณ与西亚的胡姬酒肆,有日本的遣唐使,有天竺的僧人,这里有世界各地宗教的教堂在同一座城市和平相处,甚而在西方早已衰亡的拜火教也在长安觅得了栖息之所。期盛况岂是20世纪的纽约所可比拟的。
曾几何时,世界的天平还是倾斜,李白也终于遁入传说,当历史又碾过了一个千年,大明宫的万国来仪成了圆明园的烈火纷纭,风沙掩过了飞将军的马蹄掩过了苏武的皓首,胡马不度阴山而英美却从海上袭来,长安退入了幕后,北京却遭受着战火的遍遍洗礼,曾经的属国反复上演着排华的浪潮。汉语不再由文豪们导演而成了无数出海的华人苦工们口里的唯唯诺诺。♋
英风美雨卷遍世界,被世界浪潮所击碎的不是汉唐,而是明清,是自诩“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天朝上国,文字狱愈演愈烈,思想界万马齐喑,宁古塔已有人满之患而“片帆不许下海”的命令被反复强调。继而是西方文化的强行闯入,碰♫撞激荡,反抗而后屈服,不屑而后沉默而后接受。时至今日,外语的重要程度与存废与否依然是争论的焦点,一些人主张穿唐装,废外语,尊孔教,恢复繁体字,以此作为复兴民族文化的不二良策,认为民族文化之萎靡全因外来文化的引进。
汉字听写大赛再一次让人们将矛头指向外语,看到外来的石屋恨不能将其碎尸万段,甚至于要将现代汉语的了呢啊嗯也改为之乎者也。而来到中国传统的起源与核心,来到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圣地,却发现我们的祖先全然不是这般的狭隘,孰知连李太白与唐太宗也带有外来的血统。
站在西安城口,东西环顾,东洋的日本彼时弯下谦恭的腰际,向长安派出一批一批的遣唐使,而长安也全部接受,任由他们将长安复制成奈良。西望阳关,烽燧连天,黄沙漠漠挡不住袭来的驼铃清脆却摇撼着时代的神经。长安街头必是行走着许多高鼻深目的外邦人的,而这些人不仅可在长安自由活动甚至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出任官职,许多人最终成为大唐高官,在西安可以找到不少异国人的墓碑。如是种种,中国文化最璀璨的时间是在唐代,世界各国的华人聚居地名曰“唐人街”,唐装唐服,唐诗唐散文唐传奇,无不成了民族文化永远的印记。唐人如果看到金人为了复兴民族文化而排外又当作何感想。
长安之伟大在于其包容与开放,海之广阔也在于其百川并纳,而固步自封,闭关国门自然也是民族衰落的前兆。中国自宋亡之后开始被世界赶超,正因为宋亡之后民族的气度愈加狭小,因而面对列强不复再有当初驰骋漠北,燕然勒功的英风豪气。今天的民族欲重新撼动世界,又怎可以重蹈明清的覆辙。
汉语与外语绝非两不并立,不禁想起一百年前,救亡图存的呼声将古老的中国遍遍捶打。辛丑条约的重负尚压在肩头,列国的公堂,戊戌的朝堂被时代风浪卷挟奔腾,清末新政未及实施ข,辛亥革命便已掘开了旧政权的坟墓。与此同时,中国有一个大师林立的时代悄然来临,文学、思想‘历史’哲学‘科技诸多领域忽然绽放成了绚烂,初醒的民族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减轻疾病缠身的苦痛。阿Q成了国民的镜子,清华、北大、燕大成了学术的中心,抗战后西南边陲的联大更是中国教育梦幻般的所在,那些在国学上造诣颇深的学者,那些修纂着中国哲学史文学史思想史宗教史,潜心研究着孔子老子庄子乃至柳如是的大师们,细察之下,竟然精通着多国的语言,英法美日德,甚至于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他们的学术成就依旧是当今的楷模,而他们的外语水平又令人瞠目结舌。细细想来,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究竟潜藏于怎样的时代,怎样的个体,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究竟潜藏于怎样的时代,怎样的个体,民族文化之复兴又究竟依靠于怎样的思想与观点,当我们站在当今的时代,去回眸细数那些民族文化的高峰,必可以发现它们无不依托于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广阔的胸怀,一种博大的气度,也必可以发现在历史崎岖的道路上,在民族蹒跚而坚定的步履中,如何☭开启一个民族文化的复兴。
长安毕竟已成历史,汉唐在视野的边缘渐行渐远。21世纪的民族文化将在一个开放而博大的国度中走向复兴,当千年后的人们回首我们的时代,他们的眼眸中是否也会出现一种向往与骄傲的炯炯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