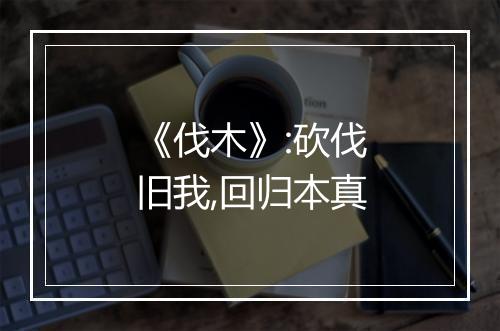《伐木》:砍伐旧我,回归本真
由波兰国宝级戏剧大师克里斯蒂安 ・陆帕改编自奥地利作家托马斯 ・伯恩哈德同名小说的话剧《伐木》,在即将去法国参加阿维尼翁国际戏剧节前夕,在天津和北京隆重上演。历经长达四个多小时吊诡、高冷、困乏的剧场旅行后,京城的戏剧艺术圈暴土扬烟地刮起了一场文化风暴。这位欧陆戏剧巨人破坏规矩,撕裂面具,揭穿谎言,粉碎尊严,把中国最核心的艺术界人士悉数搅合到被嘲讽谩骂的艺术群落里去了。
一场批判的艺术晚宴
深夜十一点,维也纳一群名流艺术家们在一所精心布置的波西米亚风格的华丽宅邸里枯坐。这群音乐家、作家、演员和画家喝着香槟,弹着钢琴,借口缅怀 20多天前自杀的女演员乔安娜,空泛肤浅地谈论着艺术和人生的关系,焦急等待着一位大名鼎鼎的国家剧院演员。上半场是“等待戈多”,下半场是“最后的晚餐”。国家剧院演员终于来到,有巴拉顿湖鲈鱼的晚宴在杯盏交错中开始了。然而美食美器、蓬荜生辉的艺术沙龙却遮不住空洞乏味,各位艺术家在互相嘲弄和鄙夷后,暴露出行尸走肉一般绝望丑陋的真嘴脸,最终分崩离析仓惶散伙。作为“沉默的在场者”的男主角托马斯 ・伯恩哈德既是参加聚会的作家、乔安娜的密友,也是小说家和导演☣陆帕的化身。他冷冷地剖析着每一个人,在自己流动的爱恨交加的情绪中诅咒着他们又怜悯着他们。主观视角的变动与客观行为的改变组成了多重理解上的排列组合,心情在懊丧、愤怒、冷漠、无奈中反复徘徊。
整部戏是以影像开始的。一开场,灯光并没有暗下来,舞蹈家乔安娜的采访录像被投射到框架上方的幕布上开始播放。记者问她“为什么要教演员如何走路? ”“为什么要离开国家大剧院时”等问题时,她的回答显示着一种决不妥协勇往直前的艺术观念。这样纯粹的艺术家却遭受失业、孤独、爱情劈腿等艰难困境,最终不被容于这个世界。那些晚宴上信口雌黄腐朽僵化的伪艺术家们却拥有着所有荣誉和优渥享受。
这部剧是给伪艺术家们的一记响亮耳光,也是为真正艺术家准备的一场葬礼。当伯恩哈德走到和观众最近的那道红
线后,痛恨咒骂那群艺术家的时候,灯光亮起,观众席突然被作为舞台的互动参与空间,和舞台并行呈现。那些谩骂和讥讽直指现实,艺术铁粉们如坐针毡,无处逃遁导演陆帕和原作者伯恩哈德批判的是“精英文化”对人的天性的伤害,而会刷夜看《伐木》并痛苦到黎明的人群,也恰是剧里批判的那个群体。
演出后的若干天里,京城各大媒体充斥着对《伐木》的深刻分析、智慧领悟和溢美之词,评论者们努力地从引证《诗经》推至“气场”、“大道至简”等抽象深奥的审美高度,充满想象和才情,精彩纷呈超过了演出本身。北京剧坛宛如又一场台下的艺术晚宴,抑或膜拜神坛,似乎行尸走肉心安理得的多年幸福,被这么一刺激果真醒狮一样腾空而起,众口铄金直到让地球裂开了一道霹雳裂缝。
剧中对国家剧院、主流艺术圈、政府体制的批判引起了中国观众的强烈共鸣,尤其是下半场伯恩哈德几段爆发性的独白,赤裸裸怒斥了和政治权力媾和的艺术家。
“为了向卑劣的国家阿谀奉承,比尔罗丝和雪尔可都很快地放弃了她们的初衷、梦想和热情,她们开始向评议员、部长、其他文化部门的官员们溜须拍马当她们的文学处女作发表成功后,她们就立即背弃了自己和文学的初衷这些人在无知的政客面前,永远随叫随到所有的艺术家迟早向这个脏污又残忍的政治环境投降,大部分甚至马上就缴械了,我们的艺术几乎变成了和国家打交道,我们所秉持的
艺术道路,不过是充斥着卑鄙又虚情假意的实用主义 ”
托马斯这段愤怒的独白,深深地谴责了整个体制,数度在剧场掀起热烈的掌声。看来艺术家在全球都是惺惺相惜的――伪艺术家经常在自己不得意时,把罪过推给体制,当自己得到体制的青睐时,又会瞬间忘记关于艺术的梦想。
在剧组和观众的交流环节中,一位戏剧人以激越情绪向陆帕提问说:“中国在艺术高于生活的理念下,产生了大量说谎的、反艺术的作品,中国戏剧市场资源的被占有率和浪费程度都是天文数字。当你面对大量这种说谎、欺骗的情况下,你会怎么表现你的创作元素? ”这种贴标签式的强制提问,不过是在借着陆帕振臂高呼,表达愤怒。无独有偶,一位文艺青年质问道:“为什么要拿这出戏伤害中国文化界,你明明知道是这种情况! ”无疑,对陆帕过于中国化的狭隘解读,满足了当下文化人发泄愤懑的需要。现场如坠冰洞,人们尚在惊悚无语中,陆帕侃侃回答道:“我并没有攻击中国文化界,我不是为中国创作这出戏,我只是把它带来中国。环境创造了我们,如果我生活在中国,我会采用很多在中国特有的、但我现在还不认识的创作元素。假如我现在住在中国,我需要很长的时间认识这里,我才能知道哪些特别有趣,哪些特别讨厌,我才能知道我要创作什么。作为走马看花的一个旅行者,马上下结论,那太傻了!真理跟谎话的关系是互相关联的,这不只在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模一样。我不知道在中国那种谎话是什么,
但是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谎话,文化自身都面临这些挑战。所以托马斯就是一个研究自己国家谎话的人,他是打败谎话的勇士,也为此付出牺牲。 ”
戏剧是一艘驶向新生活的大船
对于陆帕来说,戏剧是一艘庞大的船,带领人们渡向彼岸,去重新认识生活。他认识到语言本身充满了无力感和匮乏感,他在剧场里既探测舞台语言的新边界,也在锤炼观众的接受边界。时间的表现,影像的平行穿插,空间转换的意味,深刻的心理分析,音乐音响的运用,人物絮絮叨叨地重复台词戏剧本体的厚重远比政治讽喻更寓意丰富。一个可以围绕中轴旋转的立方体舞台和舞台上方一块大屏幕,割开了几层的时间和空间。
玛雅 ・奥斯伯格夫人对自己的内心期许是一个永远雍容华贵的沙龙女主人,她并不一定看过易卜生的《野鸭》,但并不妨碍她一遍遍热情澎湃地重复这个话题。尽管她的言语只是咿咿呀呀无法深入的粉丝腔,由于无知还差点穿帮露馅,忘记了这个男演员在剧中的名字。“艾克达尔,我们的艾克达尔”,她整个晚上无比亲密地称呼的这个人,其实八竿子搭不着,只是要标榜自己拥有着一流品味和圈中地位,才邀请他来聚会上胡吃海塞、高谈阔论。 她一张老脸上假钻石耳坠闪闪发光,以舵主之便一会儿换一身晚礼服灿然登场,腰身赘肉但不妨碍她风情万种亭亭玉立在钢琴旁,随时要高歌一曲英国时髦古乐,三更半夜,还要抖落着贵族范儿端上鲈鱼,演习一遍高雅仪式。只可惜她的愿望不是被笨手笨脚的女仆打翻器皿,就是被粗粝乖张的酒鬼丈夫和人对骂搅了局。而后半场,每个人都暴露出了空虚、枯竭的真实面目,无论她如何涂脂抹粉,也盖不住这群行尸走肉的惨淡萎靡,连金色盘发也胡乱披散下来。在送别托马斯的门口,她低沉决绝地嘱咐托马斯“别写这个”――这样一个整晚上佯装美好的人,其实对一切丑陋心知肚明,只不过习惯性地扮演着老天真、老甜心。
所到之处都要大言不惭称自己已经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 ・伍尔夫在写作上“跨越了一大步”的珍妮,虚情假意地怜悯自杀的乔安娜,言必“写作是治疗人生创痛的良药,她要是能写作,一定不会自杀”无非是通过揶揄死者、抬高自己,再一次提醒各位自己具有写作成就。“一定要从文学作品深入人物”、“我研究过戏剧理论,埃德加尔才是比艾克达尔更深刻的人物”成为她对抗国家剧院男演员、夺回话语权的一种武器。我们何其熟悉这种打着文学大旗,处处显耀自己、贬低别人的“优良传统”。
而那位让大家翘首引盼烦躁傻等的国家剧院著名演员法兰兹,对他成功扮演“艾克达尔”喋喋不休、慷慨陈词、不厌其烦地总结归纳,也真是让人醉了。他带着无上权威的脸活活是一张橡皮面具,令人作呕的同时,也为他的愚顽僵化无语到骇然。
乔伊斯和詹姆士,除了嗤嗤讪笑和窃窃私语,不会说出半句语义明朗的评价。拿讪笑作为高人一等的优越特权,貌似能站在文化的制高点上藐视众生,以戏谑嘲笑一切困境,表面上温和善意,其实圆滑而懦弱。这正是这个时代大行其道的年轻艺术家的写照。视频谈话揭露了这两个躲在卫生间里的文艺青年其实焦虑着大到创作动力、小到对待葛汉 ・奥斯伯格的所有问题。
伯恩哈德的批判目光对自己也是犀利的,明明知道乔安娜自杀的必然,赞成她的生活态度,也未能免俗地在葬礼上乔装悲恸。
舞台上被碎碎叨念的是音韵重叠的名字:“艾克达尔”、“我们的艾克达尔”、“艾德加尔”“塞巴斯蒂安广场”,就连不断提及的《野鸭》,在波兰语中也是叠音的词语“卡赤卡” 这些嘈嘈切切絮絮叨叨、兜来转去绕来绕去的阴险叠音几乎把观众整疯。伯恩哈德和陆帕都擅长运用声音的重复控制舞台节奏,形成一种梦幻迷离的语境,迫使观众的情绪被不断挤压到接近爆裂。演员们始终如同窃窃私语般的独白,保持着超低的音量和超慢的语速。轻叹、哼笑、鼻息这些声音的“微表情”也被放大,配以音乐音效,整个剧场仿佛被催眠,进入松弛的潜意识状态。
这是陆帕自己在幕后用话筒音效参与演出,控制节奏。他解释说,声音能够给演员一个刺激和诱导,声音也具有色彩和质感,甚至能传导温度,能影响表演的体验、演出的进程。
全剧的华彩段落随着《波罗莱舞曲》让压抑的情绪盘旋往复。全曲以一个巨大的“渐强”主题发展,在小鼓无休止的三拍子节奏背景上,由各种乐器∞演奏的两个 17小节的旋律回旋上升,令人眩晕痉挛,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戛然而止。艺术家们如同一堆堆烂肉瘫在沙发上,目光呆滞,形若槁骸。所有对艺术、精神、创作、生死的讨论在失败的人生真相下溃不成军。
每到幕间换场,由人推动的巨大玻璃体如迷宫一样交错凌乱,演员们如同迷失在玻璃森林中的各种动物,栖栖遑遑,四顾茫然,无处归隐。就连不断被提及的戏剧大师亨利克 ・易卜生出版的转型剧作《野鸭》,也是和《伐木》对称烘托的。《野鸭》同样开始于一场宴会,是为了欢迎离家十多年的独子格瑞格斯的远道归来,记叙了生活真相被揭露后引起的一系列家庭惨景,似乎暗示美好生活需要谎言的粉饰。这部易卜生所有戏剧创作中颇为令人困惑和茫然的主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时时处处都充盈着由各种谎言和假象所构成的幻景;我们陶醉和浸淫其间,只要没有人来捅破它的虚幻性,生活还是可以平静而快乐的;只有看清事实真相才能让各自心中的“野鸭”毒气得以释怀。
剧中有太多技术和形式上的细节可以反复体味。演出中经常出现的大段静默,通过影像所塑造的另一重时空,“过去时”或同一时刻发生在不同空间里的“进行时”使得空间和时间像一张逐渐被铺陈织补的蛛网一样无限张开
戏剧与小说的艺术理念一脉相承
投影和时间这两项元素向来是陆帕的拿手好戏。 2014年陆帕因为林兆华的邀请带着《假面 ・玛丽莲》第一次来到中国,投影机为舞台带来虚幻的投影,仿佛梦境交织。在陆帕的计划里,玛丽莲原本只是“假面”三联画的第一部分――整个三部曲将会是一个长达 9小时的持续作品。他的《马耳他》曾经连演三晚,《卡拉马佐夫兄弟》(7个小时)曾获奥地利十字功勋奖章、法国文化部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欧洲剧场大奖。在这个满头白发的波兰导演的手中,时间与灯光、影片一样,成为其剧场表达的一分子。
在波兰剧场史上,陆帕承接康托、格罗托夫斯基,下传瓦里科夫斯基的枢纽地位,痴迷于维特卡西和荣格派心理分析理论,重视探索剧场的感知能力。于他而言,剧场是一种探索和反抗人类个体疆界的工具。他的作品致力于关注 “人”,以个人(角色)为观点,探讨其存在的心理、社会与历史关系。陆帕总会以巧妙方式将不同的阐述方法汇整一致,创造出精准与清晰的观念,尤其是擅长透过延长、缩短与停顿等手法,让时间成为角色状态的表达方式,将剧场转化成一种存在与知识论的经验。
陆帕的生活经历也异常折腾,不是自己退学,就是被学校开除。他在欧洲最古老的亚盖隆大学学习了两天物理,就退学考入当地的美术学院,又用两年时间在罗兹ซ电影学校学习电影导演,因为艺术观念的反叛被开除,直到 1973年进入克拉科夫国立戏剧学校学习戏剧导演。所以,《伐木》的舞美和灯光设计都是陆帕亲自操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念贯彻到所有细节上,一丝不苟,不惜代价是他创作的一贯风格。以心理学家荣格为精神导师的陆帕,精于剥开层层“假面”,直抵人性幽微之处。他与每一个演员建立密切的关系,引导他们寄居到角色的身体里,同时要求“演员要与表演做斗争”,尽可能在剧场中寻找真实。 说到陆帕的艺术理念,不能不说到以桀骜不逊著称的 “是非作家”伯恩哈德。托马斯 ・伯恩哈德这个名字在德语世界乃至欧美,是一个名震文学艺术界的名字。他曾先后获得过数十种重要的文学奖项,包括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毕希纳文学奖、奥地利国家奖等。但他本人觉得索然无味,拒绝接受任何文学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伯恩哈德曾多次因《伐木》写得太露骨而引起一堆口水是非,曾经的朋友、音乐家盖哈德 ・兰佩斯贝格因此书起诉他,使该书被警方收缴。但这部小说因此声名大噪,同时也造成伯恩哈德与他的祖国对抗。 1968年,在接受奥地利国家奖的仪式上,他毫不留情地抨击奥地利的政治和现实。
伯恩哈德所描写的英雄是一个疯子,总是站在“正派”的对立角度去批评服从所谓当代价值观。伯恩哈德不能容忍艺术被文明同化,不能容忍文化人的谄媚让文化统治者对自己的行为产生错觉,权利明明是在损害艺术,却自以为是在进行文化建设。关于整个文化艺术的生存环境,是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对抗,也是艺术家自身理想和现实欲望的对抗。而也有观众会从中看到,剧中所有艺术家们遭遇的精神困扰,其实也是每个普通人都会遭遇的。伯恩哈德像一副利齿,他不断地咬啮着人类的自我欺骗、伪善的神圣价值观以及所有ณ的宗教方面。伯恩哈德以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化身社会和人民的牛虻。我们精神上的活动都是虚伪的文明,这部作品在攻击、逼迫读者去改变原有的想法和观念。
这两个主题彻底地颠覆了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的艺术活动。陆帕如是剖析伯恩哈德作品的精神内涵。陆帕从八岁就认识到没有上帝。天主教在今天已经沦为批评别人、彪炳自己精神领袖的一种工具。正如剧中那些动辄满口艺术,以此ค来评判他人、显耀自己的文化人一样。他改编很多外国文学作品,总是被民族主义者指责“不爱国”。陆帕从不认为有取悦观众的必要,因为如果一部戏所有观众都喜欢,那就说明戏剧中没有新的东西。阅读一部小说,里面有很多厚重丰富的层次,需要一层一层去展现,去经验,去体悟。他希望用他的戏剧让观众去旅行,从头到尾地体验所有。
说起“伐木”的字面意义,通常这个词是以德语发音,舌尖上滚动而出、划过空气之间,就传达着一种果决颠覆、震撼警醒的感觉。《伐木》的提示在于:任何使得理想被钳制、被困顿的东西都应该被砍伐掉、清理掉,人应该不断砍伐虚伪腐朽之树,永远保持着否定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唤醒最初的理想。高耸入云巨大树木的倾斜、翻转到轰然倒地,带给人极大的震撼。艺术家被权力、体制、利益、伪艺术家们收割,面目全非,横尸遍地。我们自己已经成了空心的腐朽之树,必须被更新被砍伐掉,虽然这是极为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