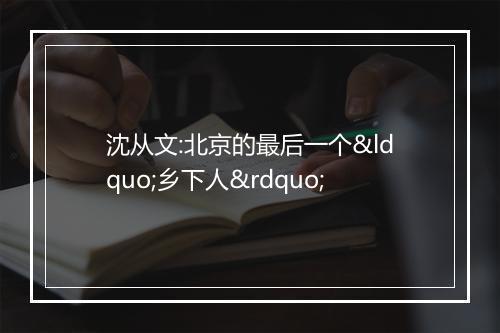沈从文:北京的最后一个“乡下人”
半个多世纪以后,这句话依然炙手可热。从此,沈从文这个名字便向湘西风景如画、民俗淳朴的边城作永远的告别,而进入了北京城的记忆。
沈从文刚来北平的那年冬天,困顿在湖南会馆一间没生火炉的小屋,弹尽粮绝,连棉袄都买不起。幸而郁达夫根据一封信冒着鹅毛大雪找到了这位陌生的文学青年,发现他在用冻僵的双手伏案写稿,于是立即解下自己的围巾替他围上,然后领他出去吃饭,并把衣兜里剩下的几块钱全给了他……
沈从文20岁以前长期➳在湘西一带小码头流浪,如他自己所说:“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这条水上(沅水流域)毕的业。”北平对于他,不过是一座继续流浪的城市,只不过乡村流浪汉变成了城市流浪汉。
青年沈从文的性格魅力是流浪造成的,包括他大多数作品的素材,都取之于早期流浪的阅历,从旧中国农村的水路、陆路直到都市的柏油马路,流浪汉的心永葆青春……青年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著名的流浪汉,有人曾拿他跟马克・吐温相比,根据年轻时相似的经历,笔者觉得他还有高尔基《在人间》及《我的大学》时期的影子。
然而四年未满,沈从文就因军阀张作霖在北方制造白色恐怖,随同冯雪峰、丁玲、胡也频等一批青年文人南下,移居上海。三年后返回北平,因胡适的推荐,在中国公学任教。1937年,因卢沟桥事变随同清华、北大师生(当时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南迁昆明。两度离开北京城皆为避难。
1946年,沈从文携家眷绕上海回光复后的北平,其后半生便完整地属于北京城了。
沈从文三进北京城,最终回到北京,是颇受欢迎的,子冈当即在《大公报》发表《沈从文在北平》一文,兴高采烈地告诉读者:“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件灰色或淡褐色的羊质长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子上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数,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在他眼中,刚刚从沦陷的历史中挣脱的焕然一新的北京城,亦将因沈从文的重新出现而增添那么一丝光彩。
沈从文生长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的文风与人格都带有蛮荒之地所孕育的淳朴与野性,如施蛰存所说:“……在他的早年,中国文化传统给他的影响不大。这就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题材、故事和人物理解的基础。各式各样单纯、质朴、粗野、愚昧的人与事,用一种直率而古拙、简净而俚俗的语言文字勾勒出来……他的文体,没有学院气,或书生气,不是语文修养的产物,而是他早年的生活经验的录音……这是一个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
沈从文一贯自称是永远的乡下人,甚至在向张兆和求ง爱时也诗意地表达“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心有灵犀地给他回了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弄得发报员好生奇怪,猜不出是什么暗号。
他移居北京后,接受了城市文明,跟知识分子中的绅士派广泛交往,沾染了不少绅士气,但仍然带有乡村绅士的倾向:“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他在绅士派中间,还不是一个洋绅士,而是一个土绅士。”(施蛰存语)
他成为北京人后,由于血统与身世的缘故,依然是一个复杂的北京人,或者说是一个复杂的北京文人。当然,沈从文自己意识不到这点,1933年他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把南北作家划分为“海派”和“京派”,褒扬京派而贬低海派,并自居于京派之列,诱发了一场轰动南北文坛的大争论。沈从文作为“海派”与“京派”之争的始作俑者,对自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京派文人不无自豪。
李辉转述过陈思和在《巴金传》中对20世纪30年代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京派文人的评价:“这些以清华、燕京大学为中心的几代由作家、理论家组成的文人,是在‘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形成的。”他进而联想到:“这种自由主义传统,是否也包含着这样一层含意: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作为一个个体,在构造自己的文学理想的同时,将一颗不安分的灵魂,同源自湘西山水的性格结为一体,该是同样的美妙。这种不安分,后来被以寂寞表现出来的一种平和所湮没了。人们更多地看到的,只是他并非出本意的与文学的疏远,以及久久的沉默……”
李辉把沈从文身上的这种不安分称为“极为难得的‘五四’传统”,这自然与沈从文生活在爆发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城,以及他个人努力弘扬京派文人的精神不无潜在关系。
沈从文后半生是寂寞的,简直跟他的前半生判若两人,北京给过他辉煌,也给过他萧瑟。虽然他的后半生属于北京城,但解放以后由于一言难尽的原因,他出人意料地告别了自己的文学时代。他改行美术考古学,在故宫博物馆的青灯黄卷中浮沉,由文学转向学术,另一个沈从文出现了,并推翻了自己的前身。
沈先生的后半生,是在自己的文学废墟中凄凉地度过的。当然,他也在废墟中一砖一瓦地堆砌起另一座全新的宫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以说他并不是完全的失败者。黄苗子曾评价过沈先生后半生在文学上的荒芜(即作家身份的过早终结):“可是沈先生对于这一点,他并没有介意――至少在表面上。他永远兴致极高地谈他的美术考古……沈先生是否就永远忘记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了呢?并不。最近我同沈先生谈起,在国外,有一位研究他的文艺作品的学者得到了博士学位。沈先生羞涩地笑了一笑,大拇指按着小指伸出手来,轻声地更正说‘三位了’。” 幸好他后半生撰写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称为“前无古人的巨著”。他不再剖析今人♋的灵魂,改而研究古人的服饰。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他在北京城里一段人生的结晶,可算献给这座作为其生命归宿的城市的一份厚礼。他的得意门生汪曾祺说:“沈先生五十年代后放下写小说散文的笔,改业钻研文物,而且钻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国人、外国人都很奇怪。实不奇怪。沈先生很早就对历史文物有很大兴趣。”
黄苗子也曾辛酸地描绘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沈从文:“天安门城楼上的男女厕所,沈从文认认真真地天天去打扫(后人如写‘天安门史’,应该补这一笔),他像摩挲一件青铜器那样摩挲每一座马桶。”
“文化大革命”期间,沈从文留存的自己著述的样本被全部销毁,他好像并未感到可惜,更不加以回忆。✡云开雾散之后,沈先生的传记作者凌宇前去采访,惊讶地发现:“时间过去了三十年乃至半个世纪,许多作品及一些笔名连沈先生自己也忘却了……我偶有所得――那些以沈先生忘却的笔名发表的作品,便请沈先生加以验证。”
据说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形,凌宇说出一篇待验证的作品名称,沈从文摇摇头:“记不得了。”于是凌宇便复述作品的内容。还不等他说完,老人便孩子一样天真地拍起手来:“是我的,是我的!”他笑着,眼里有了泪花,似乎很高兴。
以《边城》为代表作的沈从文,是属于北京城的,又是永远属于湘西的边城的。他永远是边城的哨兵。沈从文的故乡是湖南的凤凰。他本人就是一只凤凰,一只能在烈火与灰烬中获得新生的神话之鸟。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他从蛮荒的湘西第一次来北平时,肯定有一种“进城”的感觉。他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来到城市后通过回忆写下的,主题依然是魂索梦绕的乡情民俗。因而获得了双重身份:既是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又是一个不断怀念着乡土的城里人。
他即使在干燥寒冷的北方城市,文笔仍然凝注着旧中国南方农村河流与泥土的气息乃至巫鬼诗情,仿佛刻意要为城市读者创造一个乡村的神话。沈从文不曾割舍自己灵魂的根须与远方广袤原野潜在的联系,他的乡土情感是真正的城里人(或城市文人)无法想象与比拟的。他既为旧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吟唱了一曲划时代的挽歌,又为缺乏想象力的现代城市生活馈赠了一首天外来音般的田园诗,炊烟弥漫的乡愁因为都市背景的烘托而愈显缠绵悱恻。
他不仅是乡下人,更是乡下的诗人,一位农民式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仅是城里人,更是一个反复咏诵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的城里的隐士。至于他的后半生,又做了北京城里的文学隐士,告别文学而归隐,隐逸于秦砖汉瓦、青灯黄卷……
沈从文曾于20世纪40年代写下自我预言:“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命定的悲剧性。”笔者估计,随着现代大工业文明对乡村精神的蚕食与消化,又有谁敢于把乡土情感视若至高无上的精神财ว富,至少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它已接近于没有传人的遗产了。
所以,沈从文,也将是中国文坛上的最后一个“乡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