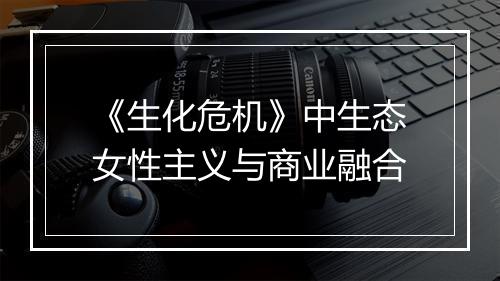《生化危机》中生态女性主义与商业融合
[摘要]当前,生态叙事已经成为商业电影的一大看点,但“高票房低评价”也成为许多纳入生态元素的影片中屡见不鲜的现象。本文以《生化危机》系列电影为例,分析其对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框架的引用如何吸引了观众的阅读期待,丰富电影的商业看点。而对商业的过度追求也导致了该影片在艺术处理上的粗糙和各种致命伤,妨碍了影片取得更大成功的可能。通过分析《生化危机》系列电影的成功与失败,可以透视作为消费文化现象的灾难片热潮,并对真正的生态电影的未来提供有益的思路。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商业电影;男权;女性形象
结合了生态意识、科幻想象与恐怖效果的灾难片已经成为好莱坞最受欢迎的一个电影类型。作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它迎合着也塑造着大众的审美口味与思想意识。而如何让处理商业看点与思想内涵艺术表现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它需要审慎对待的一个关键问题。《生化危机》系列电影不算是一个成功的作品,该系列从2002年上映第一部《恶灵古堡》(Resident Evil)到2012年上映第五部《惩罚》,历时已十年,尽管纳入了科幻想象、特技动作、僵尸、美女、生态等众多吸引观众眼球的元素,却始终未能将之融合成一个整体,而票房不错但评价偏低的情况也一直持续。在对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框架的套用和叙事策略的选择中,其连续发展的脉络以及在其连续性中显示出来的成功与失败,都可以为我们透视当前作为消费文化现象的灾难片热潮、并深思真正的生态电影的未来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反男权与科技批判
作为一个从事高科技产业的机构,保护伞公司带有明显的男权✫特征和统治欲望。它从事生化武器的生产,挑起各国之间的扩军备战,其根本目的在于对整个世界的控制;它的运行机制中各个环节的代表人物都以男性为主,决策管理者如肯恩和威斯克、科学研究者如艾萨克博士、保安员斯潘都是充满欲望的野心家。他们以活人做实验,把人当做工具、财产,却从不把人当做人。对于以艾丽丝为代表的女性来说,带有男权特征的保护伞公司是一切灾难的根源,毁灭了她们作为女性应有的一切美好生活。从《恶灵古堡》中她作为保安员开始,她的婚姻就由于保护伞公司的介入,不仅是假的,而且成为罪恶的一部分:掩饰地下实验室的入口。
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对科技进行反思,反对机械论的非生态技术。“父权制世界中的技术与男性气质紧密关联,技术追求理性与效率,体现为操控、控制和压迫。因此,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3]影片中的结局亦印证了这一点。第一部中的斯潘为了独占T病毒的成果,打破装病毒的试管,使病毒泄露、实验室的近五百名员工异化成丧尸,而他自己最终也被丧尸吞噬;第二部中的指挥官肯恩将整个拉昆市的市民作为牺牲,而他自己最终落到丧尸手里后连开枪自杀的机会也没有;第三部中的艾萨克博士想要取得更强大的力量,竟给自己注射病毒,最终使自己成为怪物;而威斯克的结局虽然还没来到,但相信在第六部中一定不会有好结果。伴随着男权统治的强化和技术的日益疯狂化,T病毒榨干了人们的生命、让江河湖海完全干涸、使森林变成沙漠,鸟和兽都开始变异,整个内地都变成贫瘠的荒地,地球开始衰退直至毁灭。非生态的技术毁灭了想要统治一切的男权代表,也毁灭了整个世界。
二、影片中的两类女性形象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卡罗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曾分析自然的女性形象有两个方面:一是有机论中的自然形象,有生命、有感觉、能够自我完善,“与一位养育众生母亲形象等同”,一是机械论中的自然形象,是“非理性的施虐者”代表着野性、暴力和混乱,人类需要对其进行征服和控制。[4]2-4《生态危机》系列中的女性亦可以分为两类,且基本上与麦茜特提到的自然的女性形象相对应。一类是作为人工智能系统化身出现的虚拟的女性形象和受保护伞公司药物程序控制的女性,火焰女皇、红后、克莱尔・雷德菲尔德等都属于这一类。他们身上的第一个特点正是混乱、野性和杀戮。火焰女皇为防止病毒扩散而对实验室里的所有人员采取灭绝屠杀手段已属极端,而红后对艾丽丝等人的追杀更是疯狂。同样,受药物程序控制时期的克莱尔亦毫无思想意识,只剩下杀戮本能。而对于保护伞公司T病毒项目的掌控者来说,他们却是柔顺听话的武器。当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这些形象并不是女性的本来面貌,而是男权制度下的产物。火焰女皇、红后都是有✘男性开发设计、男性控制、执行男性命令的工具,而克莱尔等亦是被代表男权力量的保护伞公司剥夺了心智。
以艾丽丝为代表的另一类女性则喻示着反抗、拯救与希望。除艾丽丝外,第一部中潜入地下实验室收集保护伞公司黑幕证据的丽莎、第二部中电视台的采访记者泰莉、第三和四部中的克莱尔・雷德菲尔德、第五部中的艾达・旺都属于这一类。她们都是男权欲望的受害者,丽莎中T病毒后成为丧尸,泰莉为揭露保护伞公司的黑幕被拘捕后生死不明,克莱尔曾受药物控制成为丧失心智的武器,艾丽丝更是受尽了保护伞公司从身体到精神的残酷折磨:记忆丧失的惶惑、实验过程中的痛苦、被植入病毒后那种变异得不像人类的感觉、逃亡过程中被迫远离人类的孤独,所有这些都在展示着男权欲望对女性的压迫。而在所有人中,唯有艾丽丝能与T病毒成功结合而不受其害甚至进化得更完美、也只有她的血清才能克制T病毒,这喻示着她具有大地母亲般自我完善的功能和不可摧毁的生命力量。
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宣称的“女性自身的生育性的生物特征使女性事实上更接近于自然,她们的社会角色是守护者”[4]2。在整个系列中,这些女性尤其是艾丽丝始终扮演着生命的拯救者的角色。丽莎和泰莉都为揭露保护伞公司的黑幕而牺牲,克莱尔在被保护伞公司沙漠化的世界里组织车队一路搜寻和救助幸存者。虽然导演并没有给她们足够的镜头,但依然令人充满敬意。艾丽丝的表现更是非凡:在教堂中救吉尔・范伦婷和泰莉等人、在学校救安琪拉・艾胥弗、在沙漠怪鸟袭击中救助克莱尔车队、在死亡之城救助卢瑟等人,类似的事件数不胜数,而在飞机上舍生救护安琪拉和第五部中救贝蒂的情景最为感人。不论是多险恶的绝境,只要艾丽丝出现,就总是带给人希望和反抗的力量。她始终把逃生的机会优先让给别人,不论境况多么危险也不会舍弃任何一人。当艾丽丝与克莱尔将幸存者带到阿卡迪亚,并以女性的声音将保护伞公司关于阿卡迪亚的骗局变为真实的希望,并最终为拯救人类这个物种的延续而与保护伞公司展开决战时,不论是“阿卡迪亚”这一地名所蕴涵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还是拯救生命这一决定,其守护者的角色都与大地母亲的形象完全融合。
三、高票房与低评价的矛盾现象解读
《生化危机》系列讲述了一个由病毒扩散而引起统治与反抗、屠杀与逃生、灭绝与拯救的故事。迎合当代人身体功能退化的心理和生活的平庸乏味,以近乎完美的特技动作最大限度地展示身体的潜能甚至是超能力,使观众得以体验那种快意恩仇的行为方式带来的快感。用丑陋可怖的反面形象和血腥暴力的打斗场面刺激观众的恐怖心理使之得到缓解和释放,这些都是生化型灾难片常用的手段。然而灾难片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单靠这些手段已很难创造更好的票房收入。据德国环境史学家约阿希姆・拉德卡揭示:对疾病的恐惧是世界史上最可怕的恐惧症之一,对癌症的恐惧是现代环境意识产生的根源。[5]因此,生化恐怖电影与生态问题可以很容易地进行嫁接。《生化危机》系列将生态、女性等思想意识纳入表现范围,这既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也扩大了观众范围而不局限于游戏迷,将T病毒对人类生命的危害、丧尸的横行与地球的衰退相联结,也产生了引发观众思考统治与压迫、商业道德、科技批判等问题的空间,从而使作品具有了超出娱乐效果之外的深层内涵。改变传统动作片中女性只是作为男性英雄陪衬的做法,将主要角色派给女性,既将生态女性主义的内涵纳入其中,美女的打斗也成为影片视觉效果的一个亮点。
然而,由于对生态主题仅停留在简单套用其框架的程度,处理商业卖点与思想艺术表现之间严重失衡,既想吸纳众多元素丰富影片的看点,在实际操作中却又偏执于打斗,致使影片无法将众多元素融ϟ合为一个整体,带有诸多致命的硬伤。
从艺术表现来说:首先是节奏웃单
一、不能制造出跌宕起伏的效果。每一部都是开头简单交代缘由,之后迅速进入游戏闯关的打斗场面,结尾处匆匆收束。从观众的接受心理来说,打斗的快感淹没了其他一切可能的感受。其次是情节☢凌乱甚至错乱。第一部中,环境保护主义者麦特身后是有一个环保组织的,但麦特牺牲后这个组织的线索亦中断,致使生态主题无法全面展开;第二部《启示录》中的结尾处是尼寇来等人救走了艾丽丝,但到了第三部中尼寇来的角色却被卡洛斯取代;第四部《来生》中建立阿卡迪亚的结局有着非常丰富的意蕴,但执著于打斗场面,第五部中又迅速回到地下实验室的闯关模式;再次是人物形象平面化,绝大部分人物形象除了能打善斗以外别无其他,而可恶的威斯克为什么在第五部中一下子就变成了为人类而战的斗士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不知导演在第六部中会作何解释。其他细节的问题更是数不胜数。
从思想内涵来说,生态主题未能充分展开,同样限制了影片的艺术水平与商业看点。首先,生态主题嫁接生硬,变异的人类、狗、鸟都只对生肉感兴趣,何来地球的衰竭和沙漠化?其次,被生化科技导致的地球退化衰竭现象无法得到充分表现,与《阿凡达》中那种自然风光之美带来的享受及其被破坏的心痛的震撼效果相比,《生化危机》系列中的概念化交代无法引起憎恨和反思,仍停留在僵尸制造的恐怖效果层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主角艾丽丝对爱情、对未来的理想等毫无表现,除了在第四部中显示出一些主动性以外,基本上是被迫应战,未能表现出那种主动承担抗争与拯救使命的神圣感和感染力。
这种种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以商业看点作为惟一的追求,过分集中于打斗场面。虽然众多元素的摄入成功地吸引了观众的阅读期待得到不错的票房,但内在质地的粗糙却无法满足观众更深层次的需求,无法上升到大片的境界,其处理商业看点与思想内涵艺术表现之间的得失值得引起深思。
[参考文献]
[2] Starhawk.Power,Authorityand Mystery:Ecofeminism and Earth-Based Spirituality[A].Irene Diamond,Gloria Feman Orenstein,eds.Reweavingthe World: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C].San Francisco:Sierra Club Books,1990:77.
[3] 易显飞.“技术―性别―自然生态”问题研究[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3(01).
[4] [美]卡罗琳・麦茜特.自然之死[M].吴国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5] [德]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M].王国豫,付天海,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