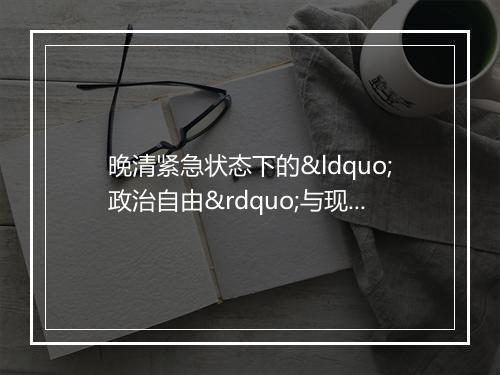晚清紧急状态下的“政治自由”与现代性的产生
" 如同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是一个以"主体的自由"为最重要特征的"方案"(Preject)。现代性是伴随着政治自由而产生的。什么是"政治自由"?用现代性哲学的生成者康德说:政治意义上的自由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1]由于现代性全面割裂、放弃了传统,在与传统的尖锐的对峙中,必然需要对政治自由的承认,因此,乌尔里希·贝克把现代性的意义源头归结为"政治自由":
"问题在于什么是现代性?答案不只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合理化(韦伯),功能性区分(帕森斯,卢曼),也是政治自由、ฝ民权和市民社会的动力学。这一答案的要点在于,道德和正义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决不是外在局部的变量,而是相反。现代性中有一个独立的(同时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的意义源头,这就是政治自由。这个源头决不会因日常使用而枯竭--实际上,它激发了更有活力的东西。从这个观点来看,现代性意味着一个传统确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正在被取代--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亦即被合法允准的个人主义所取代。"[2]
他认为正是政治自由,现代性中间那些更有活力的尝试才被激发,古曲与现代之间的联系才能被激活。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治自由可能构成了现代性的根本价值。
在晚清,现代性自由思想的展开一方面得益于海外流亡者或流学生的独立思考,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国内租界的存在。梁启超等人不用象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那样,隐身江湖以逃避朝廷的捕杀,而是流亡海外或在国内租界避祸。孙中山之所以能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3]一方面固然是他有舍生取义之勇,另一方面也说明晚清知识者反叛的特殊性:即不必落草为寇,只要踏出国门或藏身租界,就可以高谈阔论,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这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咏史》)的乾嘉学子所不敢想象也无法想象的。
这样,在空间上,与统治者持不同政见者不用再隐身江湖,而可以流亡海外以逃避朝廷的追杀,因此,晚清那些在政治上最激进的言论和行为都出自海外的留学生和流亡者;而在时间上,清政论也不得不模仿西方,与自己的反对者"打官司"。1903年,上海租界中发生的有名的"苏报"案,清政府不得不按租界法律程序控告章太炎、邹容,最后虽然清廷获胜,但"主犯"章太炎、邹容不过囚禁两年而已,清政府在租界区内无法独掌生杀大权,无力象以往那样惩治政敌,只能"自貶,与布衣讼","闻者震诧"[4]。而租界为了保护自己的"治外法权",在清廷的反对下,客观上保护了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因此,租界与使馆反映出现代中外关系的双重性质:相对于民族国家,租界是丧失主权的被殖民的标志;但对于清帝国,租界则是"政治犯的庇护所",清廷的反对者享有着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如此双重处境,被当时人(如陈天华)称为"不幸中之一幸":"各国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于国体上是大大的妨碍。那些志士,幸得在租界,稍能言论自由,著书出报,攻击满洲政府,也算不幸中之一幸。"[5]
因此,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这样,晚清存着着极其有限的"政治自由"。马克思在谈到亚洲解体的时候,曾经谈到人们对旧有宗法制社会和平生活的依恋和这种制度在客观上缺乏政治自由的弊端:
"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光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6]
因此,尽管田园般的古典令人在情感上无限依恋,但是在理性上,政治自由是告别这种田园情怀的最高价值所在。在晚清这个大"变局"中,国运飘摇,风雨如晦,内忧外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质言之,这是一种现代性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的产生一向是现代历史的症候,甚至是现代生命体验的最基本的存在感知。尤其是在被迫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只有一种,即"我们必须形成一种与这样的认识相一致的历史观。"[7]在我看来,"紧急状态"是包括影响与反应在内的两种状态,一是外部世界的紧急状态,这是由现代性全面生成和普遍扩散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问题造成了,这些问题的爆发导致了无法避免的精神、文化上的双重危机,二是身处其中的人们认识并感知到这种紧张而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紧张状态,这是对外部紧张的一种回应,也是一种强化。所以,晚清知识分子,一方面在诗文中描绘西方列强的欺凌,一方面同"物竞天择"的公理来强调这种局面的必然性和危机性,刻意制造一种危机意识,这是在民族存亡之交对现代性'紧急状况"所作出的积极反应。
中✍国的现代性这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悲剧的悖论中展开的,它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马克思用的比喻虽然形象但是充满暴力――"用人头做成的盛有甜美醇浆的酒杯"。[8]而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则用了一个更为文雅但也更让人难受的比喻,她用"一件华美的爬满虱子的长袍"来形容中国充满悲剧意义的现代性。而在欧洲,现代性呈现的多为其进步与自由的美好面孔,它的另一副面孔――野蛮与暴力早已成为隐性面孔,被作为面具强行戴到那些前现代化国家和民族"脸"上。因此,在中国这样后发现代性且又是被迫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性的正反两孔不停交换,一面是进步与自由,另一面❥则是野蛮与暴力,这就让晚清人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和不安,一方面是列强侵吞在即,另一方面,国家的不幸和苦难却出乎意料地造成了晚清人"躬逢良时"。[9]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登上日本军舰逃过帝国缉捕,流亡海外。慈禧虽出赏金十万白银亦无可奈何。使馆与租界成为中国人在国内与统治者争锋相对而不被虐杀的安全之地,这种情况在此之前不仅从来没有过,而且也是不可想象的。
正因为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一定限度的政治自由,所以清末的戒缠足以及1911年以前自发的剪辫运动才能由此展开,清廷内部分为开明派和保守派,开明派的政治主张极为激进,使得一直到现在都有学者指出:如果清廷开明派改革成功,则中国历史的发展可能会是另一番样子。
政治自由的标志之一就是晚清报刊的兴起,报刊为传播现代性观念提供了阅读上的空间,报纸不但制造了大众的品味,还制造出布迪厄所说的"落拓不羁的文人",宣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群体的产生。由于他们所加入的是商业化机制而不是传统的政治化的机制,创作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创作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体裁、题材、形式、语言的一系列转化。因此,现代性产生于艺术的自主生产场的建立之中,"导致一个场形成的过程是一个社会混乱的制度化过程,其中任何人都不能以主宰和规则、观念和合法区分原则的绝对把持者自居。"(P163)而这一切,正是来自于晚清混乱的空间所造就的有限的政治自由。
晚清有限的政治自由保障了公共空间的兴起和扩大。老舍在《茶馆》中的无意中描绘了这一空间,在茶馆老板王利发开始经营时,正是茶馆最兴盛了时候,虽然三个时代都挂着"莫谈国事"的招牌,但是在晚清时代,各个人物都在茶馆中发表自己对于时局的意见,茶馆成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公共空间",但是我们接着看到,随着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莫谈国事"招牌和字体的加重、加黑,本来有限的政治自由越来越窄了,最后是三位老人在舞台上散发纸钱的场面,这个场面既是为个人,也是为时代,更是为本来" 就有限但毕竟曾拥有的政治自由的丧失所唱的"挽歌"。老舍说自己本意是要达到"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但 "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象征在晚清时生意最为"红火",暗喻着这个公共空间曾经获得了"政治自由"的滋养。以后它每况愈下。但是正如批判他的人所指出的:《茶馆》在客观上倒是让人追念晚清时茶馆里那喧嚣的热闹。老舍也由于他对晚清暖昧的"葬送"而受到了严厉批判。
正是在晚清有限的政治自由中,"大局日非,伏莽将起",各种有组织的或明或暗的社团得以兴起,而且这些社团,也不是单单革命或保皇、共和或立宪或以简单界定的,多数人既没有归附康、梁的保皇派,也没有加入革命党,夏曾佑曾称这一派为革政派。当时的社团,较为著名的有由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组成的兴汉会在长江流域一带活动,康梁的保皇会活跃于两广,正气会、自立会与中国议会以及中国教育会活动于上海及江浙等等,张玉法先生在《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中,对清末十年间的各种社团进行统计并列表说明,据张的统计,加上海外各埠的社团,一共有668个,但这仅是最为保守的统计。1904年,商会获得合法地位,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在客观上刺激了经绅商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活动的兴盛,士绅的结社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许多原先单一的政治组织发展为多样化的功能团体。1909年,清廷制定结社集会律,承认绅商的立宪及地方自治团体的合法性,[10]但是1901年至1904年间出现的新式社团,多为趁清政府的社会控制松动,利用一点有限的政治自由空间顽强地生长。
1900年以后,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最初和最主要的原动力是义和团运动所带来的刺激,白话报刊的数量开始显著增加,其他启蒙形式:戏曲、阅报社、讲报、宣讲、演说以及各式各样的汉字改革方案以及识字学堂等都在1901年以后大量出现,民间各阶层人士自民性的努力,接着是政府大力介入,"开民智"成为晚清最流行的话语,"展开了一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民众启蒙运动。少数思想家的言论顷刻间转化成一场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11]清末也因此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类似于俄国的民粹运动。
现代性是一场社会文化的全方面的转变,涉及到所有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等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正是从晚清开始,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处于"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王韬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问题"。何谓"中国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均需要重新论证。这种论证是由西方现代性逼出来的。"[14]如果从价值理念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与西方价值理论的冲突如何协调,民族性价值意义理念和相应的知识形态如何在现代世界获得合法性的问题。因此,现代性的产生,与晚清混乱的社会里产生的有限的政治自由是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的,而❅政治自由的出现,对于中国内部来说,它是近代以来解决中国政治危机的一线曙光,而对于处在世界共同体中的中国而言,它同时又是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迫到主动的选择,政治自由使得晚清人从面对特殊的"紧张状态"到自觉进入"紧张状态",古典中国由此开始现代性的艰苦尝试。
注释:
[1] Immanuel Kant,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New York,Maxmillan,1965,P43-44.
[2] Ulrich Beck,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9, p.10。 [4] 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表》,《章太炎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229页。又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香港:龙门书店,1965。第10页。 [6]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68页。 [8]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 [10] 上述资料多出于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 [12] Martin Bernal,"Triumph of Anarchism ovwe Marxism",in Mary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rist Phast 1900-1913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19
6
8),pp,108-112.
[13]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45.
[14] 刘晓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