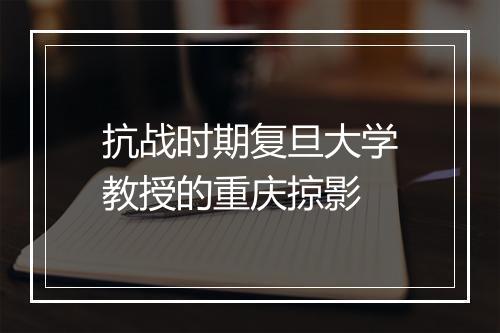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教授的重庆掠影
编者按: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复旦大学110周年华诞庆典之年。抗战时期,复旦大学历经“学府长征”入驻战时首都重庆(复旦大学当年♥举校搬迁,是驻留重庆时间最长(8年)的学校,也是目前唯一在重庆建有纪念馆的学校),不少中国的文化名人和著名教授也因此来到重庆,与之缔结了十分深厚的情缘。今逢这双重历史意义的契机,故刊此文,以兹纪念。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日寇侵略铁蹄的蹂躏,大片河山沦陷,一个国家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础之本――教育受到重创,文化事业濒临灭顶之灾。危难之际,中国大地上的教育界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大批学生流亡;二是部分院校搬迁。
当年,有“江南第一学府”之称的复旦大学700余人,历经了抗战迁校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学府长征”,来到重庆,立校在北碚夏坝。
大师风采 润物无声
1938年,我毕业于重庆求精中学,作为迁渝后复旦大学的第一批招生对象,考进该校就读于外国语言文学系。那时复旦大学学者云集,群贤毕至,堪称名师荟萃,众星璀璨。我有幸沐浴过大师们的风采,以致于7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先贤名流的光芒仍烁烁闪耀、历历在目,导引着我人生的学海航道,文山攀路,乃至终生难忘。
陈望道教授:新闻系主任,笔名雪帆,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 ت任《新青年》编辑。他不但翻译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译本的《共产党宣言》,还著述了中国第一本合乎科学语法的《修辞学发凡》,开中国近代逻辑学的滥觞。在学生们眼里,他不苟言笑,长袍裹身,一派传统学者的风度。他教我们《逻辑学》,每每上课,总是铃声响时已经提前坐到了讲台,开始点名,以君相称,温文尔雅。授课时,他极为认真严肃,但往往是深入浅出、条理分明,务使同学们在概念、判断、推理、结论等诸多方面掌握内在规律联系的基本要领,并常用理性的分析、现实的比喻活用结合,把一种严密的逻辑思维方式推置于学生们的大脑之中,使我们受益匪浅。
曹禺教授:本名万家宝,湖北潜江人,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清华大学毕业,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有“中国莎士比亚”之称。他创作的《日出》《雷雨》等名剧曾在中国抗战时期的舞台上风靡一时。课堂上,他讲授《莎士比亚》,对莎翁的全部著作了如指掌,各剧台词倒背如流。当时我们选读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他的绝活是:原文授课,边讲边演。首先自己进入角色,然后带学生们课中上戏、戏中上课,随着他那极富感染力的抑扬顿挫声调走进剧情,去触摸主人翁的灵魂,每一堂绘声绘色的讲课,就是一幕幕声情并茂的演出。我曾经就被曹教授那像魔杖般的教鞭挥舞得如痴如醉,迷恋忘返,被其带入艺术的圣殿。为此我写过一篇万言书,表达自己立志从事戏剧事业的情怀和梦想。曹教授这种率先进行文科形象化的教学,至今仍在教育改革中具有指导意义。
梁宗岱教授:笔名丘泰,广东新会人。早年留学欧洲,他精通法文、德文、英文和意大利文,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他翻译的《浮士德》,曾受到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的赞扬。他是有名的浪漫派诗人,曾主编过《大公报》的“诗刊”。生活中,他落拓不羁,在穿着上与其他教授多有不同。如夏季,他喜穿短裤和我们称之为“T恤衫”的短袖衣,行走迅速且精神抖擞,风流倜傥。他教我们《英诗选读》,上课时英语常夹有法语口音,初时我们不甚习惯,久之,倒有一点触类旁通的收益。记得有一次讲述苏格兰著名农民诗人Robert Burns(彭斯)的歌曲体抒情诗《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时,他情不自禁地把一个浪漫诗人的罗曼蒂克情怀“暴露无遗”。他用英语十分抒情地低吟起这首诗的歌曲来,感情真挚,心声醉人。这首歌是二战期间放映的美国电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歌,当后来我在90年代的一次电视演播中听见著名歌星陈方圆用英语演唱时,瞬间,半个世纪前的风云又骤然涌起、翻荡心头。那似曾相识的激昂旋律,使我立即回想起当年梁教授把这首历史名诗讲演得特别生动、荡气回肠的情景,实在感人至深。
初大告教授:原名初铭音,山东莱阳人。早年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较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如英译《道德经》《聊斋志异》等。他的英语纯熟,属纯正的英国伦敦标准发音,非常悦耳。由于较长时期受到英国伦敦社会生活风尚的熏陶,其装束及姿态也一副英国Gentleman(绅士)的模样。特别是行走时,总是循规蹈矩,目不斜视,显得派头十足,令人难以接近,远而敬之。他教我们《英语语音学》,这是一门才开设的崭新课程,因而给我的感受是课如其人,一股西方的清新之风让人眼前一亮,耳目开新。
蒋碧薇教授:她出生在江南宜兴一个世代望族的大家庭,早年留学法国,教我们《中级法语》。她是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前妻,常戴着女士洋帽和身着西式服装,那种法兰西上流社会女性风貌的打扮,颇引人注目。她的法语十分流利,发音准确,且涉猎广泛,其学识融合古今中外。加之能说会道,讲课亦细微、周到、引人入胜。
徐宗铎教授:福建人,身材魁梧,著有《中古世界史》,教我们《英国散文选读》。他酷爱读书,是闻名校内的“书呆子”,随时书不离身。一次他去成都,是一路读书去又一路读书回来,成为趣闻。他生活十分有规律,每天必定时睡午觉。为了不让人们打扰他的“白日美梦”,常用纸写上“午睡”二字贴在门上。曾有调皮的同学将其“午睡”的“午”竖笔向上拉长,成为“牛”字,于是“午睡”变“牛睡”,一时“鼾声远扬”,笑谈全校。
世纪回首 百年余音
除此以外,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还聘请了两位外籍教师。一个是英籍Robert Payne(白英)教授,一个是美籍William Collins(柯林斯)教授。
罗伯特・白英教授出生在英国一个造船师家庭,早年跟随父亲学习造船。1937年,因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慕尼黑见到希特勒,从此开始了传记写作的生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他被派往英国的新加坡海军基地服役,不久来到重庆,在战时的复旦大学任教,当时很年轻,看上去还不到30岁。他与新闻系学生张同一起住在从夏坝到么店子途中一个小山上的“鬼屋”内(此“鬼屋”至今还在,但早已“鬼”影无踪――作者注)。他教我们《英语选诗》,课余则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和写作,经常用英文打字机撰写稿件,勤奋不ถ辍。在他的授课中,一次终考我获得了100分,为此毕业离校前夕,他在夏坝新校舍门前一家小食店请我吃了一碗小面,算是祝贺。这在战争岁月,真可谓是食淡意浓啊!抗战后期他离校去了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4年我在昆明炮兵学校给盟军作翻译工作时,曾前往西南联大进行拜访。当时,他正热衷于中国抗战情况的对外报道和介绍。80年代,我从与著名作家冯亦代先生的通信中得知:白英教授曾去延安,见过毛泽东主席,后来又到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工作,并任理事。他仍然热爱中国的古文化,出版过《现代中国诗选》及两本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语译作,使中国诗词能传入美国,在中美文化交流上起了不少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来过中国访问。晚年,因心脏病在美国去世。
柯林斯教授住校外,在重庆市区美国领事馆任职,有《柯林斯精选英语词典》问世。他每周来校上课一次,随后离去。虽接触不多,因他的姓名Collins按正常音译,一般译为“柯林斯”,唯有高我一年级的外文系女同学康穆俏皮地把他译为“可怜死”,令人印象较深。
也许正因为我的学生时代有这两位外籍教师的指点,日后我一生的英语都注入了既有地道的英国音,也有地道的美国音,“两国英语通吃”专业,成为“真正的英语”而不是“中国的英语”翻译工作者。
另外,胡风教授教过我们《文学概论》课,马宗教授教过我们《初级法语》课,叶君健教授(当时笔名“马尔”)教过我们英国著名戏剧《骑马下海的人》(R☃iders To the Sea),陈子展教授教过我们《中国文学》课,全增嘏教授教过我们《快肉余生》(David Copperfield),特别是洪深教授亲自指导过我写《英国戏剧》论文。学校第二任文学院院长兼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蠡甫教授不但教过我《英国散文选读》课,1945年11月我与交通大学王德懿同学结为伉俪,在北泉公园“数帆楼”举行隆重婚礼,邀请了母校的老师同学参加,伍院长也欣然作了我们的证婚人,使婚礼格外增辉。
亲聆这些中国学界著名大师们的谆谆教诲,给我至深的感受是:读书成为了一种通向人类智慧最高境界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