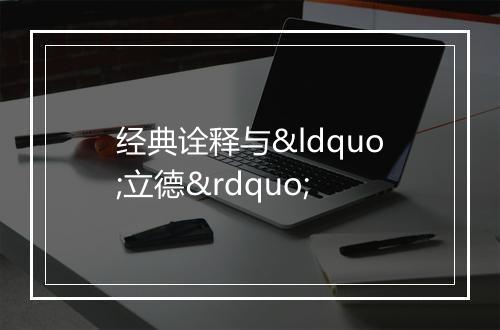经典诠释与“立德”
关键词: 文本与经典;教化;中国诠释学;立德
摘要: 文本诠释是诠释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在现代诠释学形成之前,诠释的重心是对作为“经典”的文本之理解。在现代诠释学中,诠释重心移向了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当代诠释视野中,有人甚而提出了只有“文本”而无“经典”♋。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中西双重学术视野中整合诠释传统的思想资源,以创建中国诠释学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实现的。现代中国诠释学应以“立德”为主旨,其理论形态乃是“经典诠释学”。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and “Establishment of Morality”
PAN Der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Key words: text and classics; education; Chinese hermeneutics; establishment of morality
Abstract: Textual interpretation is a central issue in the research of hermeneutics. Before modern hermeneutics formed, interpretation was textual understanding of “classics.” In the modern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shifts its focus to the test in the general sense; even some put forward the idea that there is only “text” without “classics.” Through comparison, it is conclud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ought resources in China and the West in order to interpretate Chinese hermeneutics, which can totally be materialized. Chinese hermeneutics should focus on “establishment of morality”, whose theory is “classic hermeneutics.”
一、文本与经典
现代诠释学所说的“文本”(Text)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语言性的文本和非语言性的文本。前者是指见诸文字的书写文本,以及言语性的、亦即口耳相传的流传物,如荷马时代的吟咏诗人口头流传的《荷马史诗》;后者则是指除了语言性文本之外的一切被理解对象。这种扩展意义上的“文本”的类型很多,如人的肢体动作、艺术作品,甚或自然对象,但是毫无疑问,最为重要的诠释对象是语言性的文本。在语言性的文本中,我们优先考虑的是书写文本,即便那些最初是口耳相传的古代作品,也只是借助于文字的转换才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当我们深入到各种思想与文化传统的核心时,对书写文本的理解乃是其基本线索。这不仅是因为书写文本凝结了思想使之得以流传下来,而且也因为文本本身作为思想外化了的形式,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而被分享。
在中国学者中,康有为很早就注意到了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区别,与索绪尔、黑格尔等人极力贬低汉字不同,康有为采取了一种比较平和的立场,他认为:
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皆以形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谐声略有声耳,故中国所重在形。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即分篆、隶、形、草,亦声也,惟字母略有形耳。中国之字,无义不备,故极繁而条理不可及;外国之字,无声不备,故极简而意义亦可得。盖中国用目,外国贵耳。然声则地球皆同,义则风俗各异,致远之道,以声为便。然合音为字,其音不备,牵强为多,不如中国文字美备矣。[3] 康有为所言,或多或少地揭示了中西两者文字的特点,他最终认为:西文“极简而意义亦可得”,然“牵强为多”;汉字则“文字美备”“无义不备”,失在其“极繁而条理不可及”。至于他说的“中国用目,外国贵耳”康有为说“外国贵耳”,乃是受到了佛教的启发,他说:“声学盛于印度,故佛典曰:‘我家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又以声闻为一乘。其操声为咒,能治奇鬼异兽,盖声音之精也。”(《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753页)当然,就语音中心论而言,影响更大、更具有典型意义的当是自古希腊到当代西方的哲学传统。,亦在现代哲学中得到印证。西方哲学家伽达默尔发展出了“倾听哲学”(Philosophie des Hhrens)[4],美籍华裔哲学家成中英则倡言,要以《易经》的“观卦”作为所从出发的起点建构“观的哲学”。[5]
现代诠释学™中的文本概念,通常是在扩展的意义上使用的。现代诠释学的奠基人施莱尔马赫创立了“allgemeine Hermeneutik”(一般诠释学),这里的“allgemeine”,主要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性“文本”。这种观点被视为施莱尔马赫对诠释学的一大贡献。因为在此之前,人们所关注的“文本”理解,就是对作为“经典”的文本之理解。虽然它也被称为“诠释学”,但其实质却是注经学(exegesis)。正是由于施莱尔马赫诠释学将经典的理解扩展到对一般意义上的文本的理解,才奠定了现代诠释学。
不过,施莱尔马赫虽然创立了一般诠释学,却没有舍弃“经典”概念。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仍然是经典,尤其在对《新约》解释上甚为用心。真正否定经典的是当代的某些思想家。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基于现代的价值观提出,这个世界没有经典,只有文本,并且所有文本都是平等的,他主张以民主原则对待任何文本(包括“再琐碎的涂鸦”之作在内),“使我们以一种民主的方式通向现在的文学”。[6]133这种说法虽然非常诱人,但却是很成问题的。以民主的名义将呕心沥血的精心之作与涂鸦式的文化快餐等量齐观,在其形式上虽然符合“平等”的观念,却是极为不“公正”的。在我看来,根本没有理由将“经典”与其他“琐碎的涂鸦”式的文本视为“平等”的文本。且不论就其精神价值上的差异(对文本作出价值判断显然会引起争议),我们只要观察其“生命力”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我赞同圣伯甫(SainteBeuve)的观点:
经典的理念,包含了连续性和持久性,一种形成整体的传统,被传递下去,并一直延续。[6]145
没有人怀疑,在网络文字急剧膨胀的今日世界,绝大多数的“文本”都成了过眼云烟,而只有那些被世代传诵、给人以启迪并构成着我们传统的文本,才可称为“经典”。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某些涂鸦式的文本可能有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但它们的价值只有经过我们持续的反思而融入作为整体的传统而被传递下去时,才能被辨认出来。因而,“作品”虽是某一时代的产物,但是它被认作“经典”,成为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之标识,却是后世之事。也就是说,在经过了时间的过滤而沉淀下来之后才被“追认”的。
二、经典的文学性与教化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经典”,包括了不同的类型,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经典。据施莱尔马赫:
这是从理论本身的重要性衡量经典。尽管评判经典的标准在各学科有所不同,但被称为“经典”的作品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具有某种典范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教化作用,并因此而成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尤为注重经典的“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之作用。以六经为例,它们对于人的教化之功用在于:“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教有适,其用无穷。”(《隋书・经籍志》)
这些古代典籍流传下来,直到今天仍被我们视为经典,有其深刻的原因:第一,它们保存了一个民族对于自己遥远的起源与历史的模糊记忆在这一点上,中西文化传统有所不同,西方的古代经典如《荷马史诗》等,以神话的形式曲折地映射出历史;而中国文化传统则以为经典记述的是史实,固有“六经皆史”之说。,这是世代相继的读者所由从出的根源性的东西。尽管这里所记载的“历史”(Geschichte,含有“故事”之义)并非直接就是“史实”,亦即由时间长河中“真实地”发生的事件勾连起来的“Historie”(编年史),但是它们毕竟真实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领域,构成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其二,对神的世界之描述(诸如《荷马史诗》《神谱》等),乃是以一种折射的方式表达了人类社会的价值理念,人的思维和行为规范,也就是说,规定着我们的“此在”之存在方式,这种导向与规范作用是每一个时代都需要的。因此经典不仅拥有最广泛的读者,而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们能够流传至今,就已经证明了这种生命力的存在。这种生命力扎根于人性之中,使不同时代的人能以不同方式与之产生共鸣。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作品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而且也包括作品的语言表达方式与风格,对我们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经典之所以能产生持续的教化作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就经典的表现形式而言,它们具备了卓越的文学性。正因如此,经典才有可能广为流传,为代代相继的读者所青睐,悉心诵读。在西方诠释学史上最先引起人们重视的文本,都具有文学的性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性文本中,古希腊大多数流传下来的作品,如《伊利亚特》《奥德赛》《工作与时日》和《神谱》等,都是适于吟唱的诗歌。在古希腊,尚未明确区分“诗”与“歌”。荷马将诗称为aoidē,其含义也是“歌”。柏拉图用mousikē 泛指诗与音乐。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0页。它们毫无疑问地属于文学作品。即便是“神圣的”的《旧约》,也是包含了各种文学体裁的文本。这些经典的文学价值在于,它们不仅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遥远世界之精神风貌,同时也是文学作品意义上的典范。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具有真正文学质量(literarischer Qualitt)的”文本是“卓越的文本”。[7]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意在突出诠释学与文学的那种不可分割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现代诠释学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浪漫主义诠释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阿斯特(Georg Anton Friedrich Ast,1776-1841),就是从文学和语文学(Philologie)出发构建了“精神诠释学”,他的Grundlinien der Grammatik,Hermeneutik und Kritik(语法、诠释学及批评的基本原理,1808)和Grundriss der Philologie(语文学大纲,1808),基于语文学的精神诠释学以进入文本的内在精神世界、追求“诗意的生活”为鹄的,舍弃了传统的方法论诠释学的基本主张――立足于文字考据,解释文本字面意义。 阿斯特的思维进路在伽达默尔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虽说伽达默尔学说的哲学基础是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此在本体论,但是就诠释学本身而言,他直接承继的是阿斯特的精神诠释学,而非影响更大的施莱尔马赫一般诠释学。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虽然也有语文学的因素,主张对作品的“风格(Stil)”和“类型(Art)”的作出完美理解,但其旨趣是认识论的。其方法论立足于语法学和心理学,对文本的风格、类型的分析之目的,在于更准确地解释文本的作者之原意。正是由于施莱尔马赫将诠释学定位为追寻作者原意,从而促使他努力使诠释学向心理学倾斜,这一心理学转向终使诠释学“威信扫地”。[8]而阿斯特诠释学则力图防止我们在“历史”中仅仅找寻“过去”,要求人们更多地去寻找当前的――亦即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关的――真理。[9]其任务是,在古典文化与现实之间实现一种协调,建立起新的一致性。
阿斯特显然是将古代希腊理想化了,他试图通过古典文学的研究向我们展现一个已成为过去的理想世界,在他看来,古典时代不仅是艺术的典范,而且还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典范,在其本质上乃是生命本身的范式。[12]在他那里,语文学研究的精神价值就在于它的“教化伦理目的”,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们成为那种理想的希腊人。不过,伽达默尔虽然同样注重古典文学,但是他的诠释学之目的并不在于使人们返回理想的古典世界。伽达默尔特别关注的是阿斯特所揭橥的文学之“教化”(Bildung)作用。伽达默尔进而认为,正是“教化”催生了“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教化观念(Idee der Bildung)与我们的精神存在(Sein des Geistes)密切相关:“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 [13]
三、诠释学之重构:回归经典诠释学
综观诠释学发展史,在理解的主要对象之界定上,已经历了从“经典”到一般意义上的“文本”之转折。质言之,早期的诠释学(被称为“古典诠释学”)、亦即注经学关注的焦点是经典,随着现代诠释学的兴起,诠释的重心转向了文本,有人甚至认为这个世界只有文本而无经典。诠释学家们试图建立的是适合一切文本的理解方法论体系,着眼于“文本”理解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以至于在我们尝试重新建构现代经典诠释学时,有些学者产生了这样的疑虑:我们有必要回到旧有的、已然被扬弃的经典诠释学的形态吗?理论研究的这种倒退是否可行?在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于2014年5月召开的国际诠释学会议上,成中英表达过这样的疑虑。他一直致力于诠释学的构建,尝试整合中西诠释传统思想资源建立一种新型的诠释学。在这一点上,我与成先生并无二致。区别在于,成先生努力创建的本体诠释学是一种新的哲学体系,而我的思考立足于诠释经典以“立德”,强调经典的“教化”作用,彰显诠释学的实践向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若将经典诠释学视为拟创建的“中国诠释学”之具体形态,就须先回答有否必要、是否可能创立中国诠释学这一问题。
返观中国诠释传统,自汉代以降,章句之学兴起,诠释方法论得到长足发展,逐渐形成了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考据学等学科。它们既是解经的方法论工具,也是训练解经者的专业技能之学科。解经专业化的结果,使得经学在汉代盛极一时。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有这样记载,“大师众至千余人”,“一经说至百万余言”。他转述东汉经学家桓谭的《新论》:“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尧典》为《尚书》第一篇,“曰若稽古”为《尧典》篇首四字。秦近君讲授开篇六字已是皇皇十数万言,足见其时章句之学日趋烦琐,以至于“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汉儒解经也因此被讥为“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
3
3、134页。从两汉至清代,其间各家经说各有盛衰,但对解经方法的思考与完善一直没有中断。皮锡瑞总结清代经师之贡献,计有三点:一,辑佚书;二,精校勘;三,通小学。[14]此三点所指向的正是解经方法论,而推动这种思考的动力来源于“辑佚书”。此情形与希腊时代理解方法论的兴起颇有相似之处。亚历山大里亚时代的希腊哲学家,正是在整理《荷马史诗》、圣经《旧约》等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创立了“语法学”。“精校勘”乃为所辑之佚书提供权威定本,“通小学”以辨析古今文字,也包括音训。
西方诠释学源于《圣经》注释学,在我们创建“中国ช诠释学”,所从出发的起点也无非是传统的经学。中国诠释传统,若以孔子删订六经为起点,已约有2500年的历史。历代学者的解经著述甚丰,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亦不为过。经学研究可分为两途,其一是指解释文义,运用各种解经方法揭示文本的含义,包括对解经的方法之思考;其二,阐发经文之义理,揭示其“微言大义”。当我们尝试建构中国诠释学时,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我们注意到,中国哲学、文学、历史学、法学等专业的学者,大都对理解的方法论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比如研究中国哲学的汤一介,以历史学为背景的黄俊杰,皆着眼于方法论来思考诠释问题。参见汤一介关于创建中国诠释学的“四论”,黄俊杰《孟学诠释史中的一般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第22辑)。由于他们对西方诠释学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得以借鉴其理念与方法论来探讨中国古代典籍所面临的问题。而研究西方诠释学(包括中西诠释传统比较研究)的学者,如成中英、洪汉鼎等,侧重点在于诠释学的哲学探索,力图从诠释学的角度来阐发“本体”“本体与方法”之关系、“此在”“想象力”等一系列重要的诠释哲学范畴,承继的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一脉的诠释学。
我在此尝试对创建中国诠释学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这一设想最初起因是对帛书《周易》的阅读和理解。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经学方法论的思想资源、或者沿着西方诠释学所指示的方向思考创建中国诠释学时,未给予中国解经传统的“立德”的思想以充分的关注。解经以“立德”的主旨是孔子所奠定的,他曾这样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15]
孔子解易,意在“求其德”,具体地说,为求周公之德,而并不刻意追求《周易》文本之原义。史巫也解易,可以说是与孔子“同涂(途)”。但史巫所求者为卦爻辞的原义,此所谓与孔子解易“殊归”。因儒家道统被确立为中华文化传统之正统,世代相继,而史巫之法则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时至今日,我们连卦爻辞的文义和原文读法也模糊不清了。[16]我们所能读到的,只有孔子旨在确立儒家之“德”的《周易》经义解释。也正因为孔子被视为上承诸先王、开万世之道统的圣贤,后世学者也并没有因他“求其德”式的解经方式而疑他曲解《周易》经文本义。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孔子之前本无“经”,虽然其文本已然存在,但惟有通过孔子的删订,才被“正名”为“经”。这个意义上,孔子是“经”的缔造者,而孔子之言,自然也成为“经”的组成部分。准此,孔子解易之言,也就具有不容置疑的“经”的性质,惟有他的解释才是正解。是故孔子不严格遵循《周易》的经文原义而以己意解经,实为秉先圣之大旨而自制经文。
若将“立德”确立为中国诠释学的宗旨,经典诠释便获得了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与一般意义上的文本不同,经典乃先圣所言,其义理通天道。而作为载道之体的经典,本身就具有一种典范功能,在形成我们的精神传统之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关于“德”的观念,乃出于对经典的理解及其与我们的生活实践相互印证,并由此而形成了属于某种文化与文明的大多数成员所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正因如此,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尤其是在社会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当人们试图在当前困境中寻找出路时,经典的意义便凸显出来。经典中所蕴含的先贤的智慧,属于经典所产生的时代,也属于由此发展出来的当今社会。它不仅铸造了我们的精神传统,也预示了我们未来的发展走向。倘若如此,我们要想创建中国诠释学,其理论形态当是经典诠释学,此外别无它途。
参考文献:
[2]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3.
[3]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53.
[4]Gadamer.über das Hhren[M].Gadamer:Hermeneutische Entwurf,Mohr Siebeck,1998.
[5]成中英.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1ผ).
[6]约埃尔・魏因斯海默.哲学诠释学与文学理论[M].郑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81.
[12]Vgl.Joachi☃n Wach.Das VerstehenGrundzüge einer Geschichte der hermeneutischen Theorie[M].im 19.Jahrhundert,Bd.I,S.36.
[1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4.
[14]皮锡瑞.经学历史[M].周予同,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330.
[15]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M].增订本.长沙:湖南出版社,1987:481.
[17]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六[M]. 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