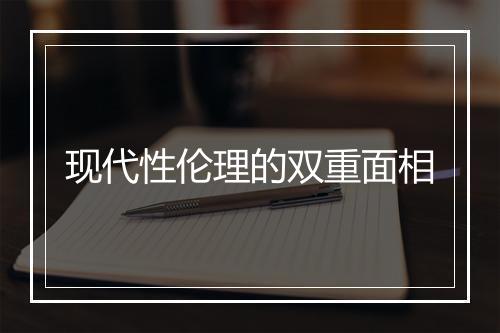现代性伦理的双重面相
"
摘要:肇始于休谟问题的现代性伦理有两个基本面相或思路,第一是理性的规则主义,第二是非理性的情感主义。第一种思路是工具理性的伦理学形式,而第二种思路则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最终表达。
关键词:现代性伦理;双重面相;工具理性;非理性主义
现代伦理是伴随着休谟问题的产生而产生的。休谟借助先哲笛卡儿“我思”的怀疑精神,第一次确切地宣布古希腊以来的独断论哲学所表明的事实与价值统一的世界处于分裂状态。在他看来,事实性知识有真假之分,可由经验证明;价值知识无真假之分,也不可由经验证明。所以,从事实推论不出价值,从表述事实的语句推论不出表述价值的语句,也就是说,从“是”推不出“应该”,或从“实然”推不出“应然”。休谟这样表述自己发现这一断裂的惊讶:“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休谟对“实然”与“应然”,即事实与价值之间一致性的质疑,在西方哲学界称为休谟问题。休谟问题对现代伦理的根本影响是双向的,那就是在逐渐消泯传统基于利他、集体、信仰以及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德性伦理之时,出现了两个仿佛相反相对的伦理面向:一是理性的规则主义,二是非理性的情感主义。第一个面相是工具理性的伦理学形式,而第二个面相则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最终表达。
一、第一个面相
众所周知,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皆源于“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所谓目的——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所谓价值的合理性,即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合乎理陛,也就是人本主义指称的符合人的本质。韦伯认为,近现代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一个价值理性不断萎缩、工具理性不断扩展的过程,即合理化过程。韦伯认为,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以手段支配目的,以形式合理性支配实质合理性的过程。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用精密的技术和计算把一切都理性化,也把人变成了机器、金钱、官僚的奴隶。他把这种由追求效率而造成的对金钱、商品的崇拜,机器对人的灵性晰民灭,称为“理性化导致非理性化的生活方式”。韦伯一方面承认理性化过程即“祛魅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帮助人们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和形而上学,以经验的、量化的形式观察世界,以科层化体系组织生产,从而带来最大的经济利润。但韦伯同时也注意到,理性化还是一个去除人的自主性的过程,人成为庞大经济机器的一个元件,理性蜕变成一种奴役人的工具。从而陷入工业生产和现代官僚体制的“铁笼”中无法自拔。韦伯说:“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显然,韦伯对人类理性所构建的铁笼充满了深重的忧虑,这种忧虑本身也正是对已逝伦理的怀念。对韦伯来说,工具理性的极端扩张,对伦理的危ว害在于使新教伦理的价值理性——比如博爱——被抛弃了。恰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信念伦理的道德一实践合理性在它得以发生的社会中无法获得制度化,从长远看,它被一种功利主义所取代”,终于形成了所谓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造成意义和自由双重丧失。"
当代杰出的伦理学家齐格蒙·鲍曼从现代性与大屠杀关系角度分析了由工具理性造成意义和自由的损失所带来的严重的伦理后果,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个案研究。在鲍曼看来,韦伯的理性化过程就是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他形象地称之为“从荒野文化走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鲍曼认为,这一过程总的目的就是删繁就简,使那些所谓信仰、迷信、不确定、情绪、情感化的东西边缘化或秩序化。也就是那些充当园艺师的人毫不犹豫地芟除园中的杂草和荆棘。现代理性培养了人类伦理对极端透明、确定和清洁的偏爱,从而产生伦理唯我论,所有那些不符合完美规则的伦理他者都属于杂质,因而在被消灭之列,大屠杀中的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他者。鲍曼指出:“在因为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雄心而显得独特的现代社会里,种族主义宣布存在着某一种群的人。他们顽固并死不回头抵制所有的控制,并不受任何旨在改善的努力的影响。”大屠杀之所以能够实施,决不是因为人类变得邪恶,而是现代性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人类对理性的高度自信。在鲍曼看来,这种自信导致人类对前现代社会固有的矛盾、冲突、芜杂、凌乱和种种问题进行“最终解决”的冲动。在此“冲动”的驱使下,种种合乎理性的高效手段应运而生,在实现最佳目标的过程中,伦理个体被迫或者自愿地协调一致去追逐一种结果。鲍曼这样说道:“我们需要斟酌这样的事实,即除其他方面外,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鲍曼认为,大屠杀的实施者并非十恶不赦的恶人,也不是心理残忍和灵魂扭曲毫无人性的人,但对理性的极端信奉使他们丧失了人伦本性。这可以说是理性在伦理上不自觉地犯下的最大罪恶。大屠杀完全符合理性条例化、规则化的要求。在屠杀者看来,被杀者不再是独特的生命,而是对抗秩序和清洁的抽象的“他者”和“异类”。同时在屠杀进行过程中,他们与自己行为导致的可怕后果之间的距离被拉大到一定范围之外,这使他们的道德冲动和对暴行的道德自抑能力不会再发生作用。这两种方式有效削弱和废止了人天生应该具有的道德责任对自身的压力。在他们所处的情境之中,道德压力完全失效而非人性被合法化,非道德行为被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技术计算和理性工具中心化,“现代性并没有使人们更为残暴;它只想出了这样一种方式:让残暴的事情由那些不残暴的人去完成”。鲍曼认为,更应当引起我们反思的是,在大屠杀的漫长过程中很少有来自屠杀者对罪行的反抗和阻力。屠杀者还几乎有些主动地与刽子手达成协作。这种荒诞情境的出现同样源自被屠杀者自我保存的理性计算能力。经过理性的严密计算和规划,自我保存的冲动成为自己行为的最高原则,包括道德冲动在内的所有其他东西都被贬低到一文不值的程度,“生命之价越攀越高,背叛之价则越跌越低。不可抵御的活下来的冲动把道德的审慎推到一边,随之而去的还有人的尊严。”理性发展到极端就是极端的非理性——鲍曼与韦ผ伯殊途同归。
但如果进一步思考的话,现代性道德这种弊端在于对同质化或齐一化理性法则或普遍规范的迷恋。同质化、齐一化是休谟所说的事实或者说科学因果范畴的规则,也是韦伯的工具理性。按照休谟以及其后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先哲的谋划,这种理性不应当越位,然而不幸的是,由于现代人对理性的过分信任,工具理性不仅越位,而且大有替代知识未曾分化以前的宗教、伦理的地位,重新统领一切领域的知识的趋向,但这不过是鸠占鹊巢的行为。古典知识型范下的宗教和伦理之所以担当那样的任务,既有知识社会学的合理性,也有合适的美德资源或者说合适的人心秩序资源作支撑。但由工具理性幻化成的规范伦理却失却了人类内在美德资源的支撑,因而对规范伦理的迷恋蜕变为一种纯规则主义的、甚至是律法主义的现代性偏执,成为缺乏内在价值动力和人格基础的纯“概念图示”,而非真实有效的道德价值资源。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德国纳粹、俄国的斯大林主义既非为了统治世界,也非为了更加富有,更不是为了所谓幸福,“它想要的只是它的意愿,它是纯粹的非理性”。昆德拉以一个小说家的声音呼应了齐格蒙·鲍曼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思考,也揭示了纯规则主义伦理的荒谬的悖反,这也是现代理性伦理最为可怕的地方。
二、第二个面相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结果,才有自觉的非理性和后现代主义伦理对此的反驳。由此产生了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情感主义、契约论的伦理观,又在极端个人化基础上,出现了叔本华的意志自由论、尼采的非道德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性道德论。至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后现代思潮,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诸如电脑网络、人工智能、器官移植、基因工程、克隆技术,以及生态环境危机等引发的道德反思,导致人类伦理观再一次对传统伦理观提出激烈的对抗和挑战。
这种非理性和情感主义的伦理路向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征。"
在价值取向上,从以往的绝对主义转向相对主义,从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从基督教的赎罪和受苦原则转向享乐主义和幸福主义,从占据统治地位的一元论和独断论转向多元论和自由论。在情感主义伦理看来,不论是伦理观念还是道德准则,除了个性化和多样化外,不存在别的理f生的或科学的本性。他们认为现代理性除了造成人性的“异化”或“物化”,使人成为机器、规则的奴隶外,未能给人带来真正的福音。多样化才真正体现人 ☻类文化的本质,对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生死存亡才真正有益;单调和齐一不仅减少人的快乐与智力、情感与物质上的源泉,本质上也是违背人性的。“利用乏味的口号、空洞的原理来兜售一种有条理、有意义的世界观,但却不能激发起人类自由,只能是孕育奴隶制度。”因为自由是不能以任何理性的教条为基础的,更不能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只能通过探求的实践才能变理想为现实。因此情感主义伦理竭力反对绝对主义、相对主义。这种伦理观认为,正是工具理性、规则伦理导致了虚假的观念和意识,才带来种种伦理灾难。而真正能破坏理性,迫使理陛告别的哲学则是相对主义。因为相对主义是合理的、人道的和广泛传播的。至于它经常受到攻击,是因为一些人一直希望用真理和实在概念来铲除它。“每一种有足够理由信以为真的陈述、理论、观点都存在论据证明与之相冲突的抉择至少是好的,甚至是更好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动态和多面的实体,其中的物质和生命、思想和情感、变革和传统将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合作。因此“现在是让理性与这种潮流分开的时候了。如同它们过去的紧密联盟一样,现在要祝贺它们的告别。”传统的真理观应向情绪屈服;不是真理构成人类行为的基础,而是ง“规范性观点和个人的特性共同构成了世界上的行为基础。后现代的同一性是由与他人的深切统一感以及与自然的深切统一感组合而成的。它同时也是由自由感和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组成的,它拒绝无条件地接受任何外在的权威作为真理之源泉”㈣。一切真理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的、一元的、独断的和纯粹客观的,而是多元的、相对的,包含着更多的主观性和情绪化成分,真理作为人类用来指导自己实践行为的一种工具,不只是过去,而且将永远屈从于激情:激情是真理的发源地,也是真理的归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激情、欲求和希望对于人生的成功和社会的进步更重要。“这些公认的价值取向为后现代伦理学奠定了基础”。对这种思想趋势,麦卡歇曾总结道:“对主体中心理性的批判,因此成为一种破产了的文化的批判的序幕。”他概括说:
“激进的批评家典型地以规则、标准以及那些在任何给定的时间与地点被理解为理性言行的东西的产物的偶然性和惯例性,来对抗用笛卡尔一康德的观点来界定理性的需要;他们以不可公度的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的无法还原的多元性,以真理、争论和价值的无可救药的‘地方’性,来对抗普遍性;以经验性来对抗先验;以可错性来对抗确实性;以异质性来对抗同一性;以碎裂性来对抗同质性;以符号的差异系统的普遍性中介来对抗自明的给定性;以拒绝任何形式的终极基础来对抗无条件性。”
应当说,这是对现ษ代性伦理价值取向上最为简练的概括。
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使社会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伦理道德革命,人们对于作为伦理主体的“自我”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重新界定。尤其是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从根本上动摇了过去坚信不疑的“自我”观念,大写的“主体”已进入“黄昏”。在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以后,福柯甚至宣告了人的死亡:
“如果这些构想消失,如同他们的出现一样,如果这些构想因某一事件而发生动摇,而该事件的可能性我们至多能预感,其形式或者征兆我们目前还不能辨别,犹如18世纪前后古典思想的基础发生动摇那样,那就完全可以打赌说,人就会像画在海滩上的一张面孔一样消失。”
一旦这个“透过自己的特殊性来感知自己为普遍性的代表”像画在海滩上的面孔一样消失,依赖于这种主体观的现代伦理自我从此走向了一条流动性的、无法统一的道路,正如特雷西所深刻认识到的:
“自我不可能再成为由存在主义者的绝望激发出来的孤独的自我,不可能再成为启蒙运动确立起来的自主自我,不可能再成为浪漫主义者的自我表现的自我,也不可能再成为实证主义者佯装的无自我。……对后现代精神而言,纯粹自主的自我已不再可能。”
由此,理性自我将成为一种纯粹自主的幻觉,通向现实自我的任何道路都必须穿越人类语言的极端多元性和整部历史的含混性。那么,拯救伦理主体的道路是否还有?正是在此疑问中,才产生了哈贝马斯的交往对话伦理和莱维纳斯的绝对“他者”理论。不过这是我们以后讨论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