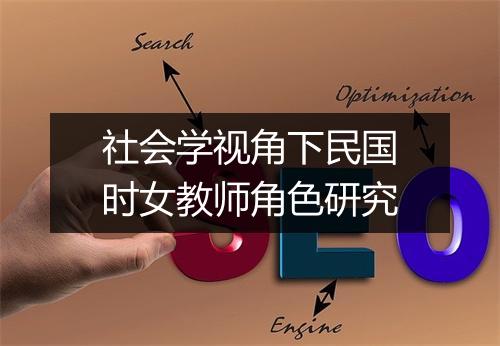社会学视角下民国时女教师角色研究
摘要: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但由于传统性别观念的固化、国家政策的介入和女性观念的异化,高校女教师面临着身为妻母与身为教师的角色间冲突,以及无法兼顾教学、科研与管理的角色内冲突。身为“新女性”,她们主要采取“独身主义”、“回归家庭”和“协调兼顾”三种方式加以调适。鉴古知今,当代女性若要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解放,离不开自身、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角色冲突;调适
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展。她们不仅要完成学术科研、教育管理等工作任务,而且要承担起相夫教子、料理家事的责任,扮演着妻子、母亲、教师等多重角色。然而,处在多重角色规范之中,大学女教师在有限的时间精力下,内心难免会产生紧张和焦虑,陷入角色冲突。
一、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角色冲突的二重表现
根据社会学相关理论,“角色冲突”是指“当个体不能满足某一角色的多重期望,或个体因同时扮演若干个在义务、权利和规范之间相矛盾角色时,内心和情感产生的矛盾与冲突”[1]。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常常游弋于不同角色间,因而往往面临角色间冲突和角色内冲突。
(一)角色间冲突
面对着社会对“贤妻良母”的推崇与对“职业女性”的质疑,才华横溢的大学女教师,既希望冲破传统性别观念的屏障,承担起独立的职业角色,追求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又无法摆脱内心深处对贤妻良母的认同,力图扮演好家庭角色。然而,时间紧迫、压力巨大,多数女教师常常难以协调身为妻母和身为教师之间的关系,在家庭和学校间奔波劳碌。一方面,繁杂的家务琐事亟需她们去处理。身为主妇,她们需要恪守操持家事的本分;身为母亲,她们需要肩负抚育子女的重任;身为妻子,她们需要完成照料丈夫的使命。另一方面,繁重的授课、科研任务亟待她们去承ต担。大ภ学女教员不仅要编纂教案、精心备课,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投身于学术研究。因此,民国时期的大学女教师,纵然博学多能,却也终日在家庭和学校之间辛劳地奔波。程俊英在回忆自己大学毕业后的生活情景时,也感慨道,“我每一个白天都是在课堂上和抚养五个孩子的家事中度过,每一个夜晚都是在埋头批改学生的作业中溜走”[2]。袁昌英在回忆写作《法国文学》期间的生活时,用一个“忙”字精确地概括了大学女教员既要为生计奔波,又要勤于兼顾家事的真实状态。鉴于女性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大学ข女教师常常需要在家庭和事业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她们渴求经济的独立,也看似脱离了腐旧的寄生生活,但家务劳动和抚育子女的重担却丝毫未减,毫无任何休息时间可言。作为“新女性”的代表,她们必然要承受着在家庭和职业间周璇应对的疲惫与无奈。
(二)角色内冲突
身处高等教育领域的大学女教师,不仅要承担繁重的课业任务,而且担任着校内一些琐碎的职务。教学与管理的双重压力,使得女教师面临着教学、科研与管理的角色内冲突。一方面,身为女教师,她们必须承担教书育人的职责。师者,须时常自省、自律、自居,方可获取学生的尊崇和拥护。民国时期的大学女教师,只有凭借其严谨的治学作风和丰硕的研究成果,才能在人才辈出的学术领域夺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鉴于生理和心理等先天优势,她们又被赋予管理者的角色。受“开女禁”的影响,民国时期女大学生的入学人数日益增加,高校女师被迫分担一些与母性天职相关的管理工作。华南女大的陈淑圭,早年留美,师从杜威,学成归国后成为福建省政府唯一的女教员。当她踏上教师岗位时,校务、教务、宗教、图书馆等后勤和管理上的琐碎工作,却花费了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致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学者,除了博士论文外,尚无其它论文、专著传世,令人叹惜。金陵女大的吴贻芳,临危受命,肩负重任,为繁杂的管理工作而忙碌,为学校的发展前景而操劳,但是她却不得不割舍心中对讲台的那份牵挂。她虽有着丰厚的教育经历和双博士学位背景,却因偏重管理而错失科研良机,实乃憾事。
二、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角色冲突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传统性别观念的固化
在被纲常伦理束缚的封建社会中,受儒家礼教的影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传统道德规范为民众所认同,“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家庭角色分工为男性所期待。民国初期,职业女性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得到男权统治阶级的推崇和溢美。然而,随着“新女性”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权力的逐渐延伸,其发展轨迹背离了传统观念下培养“贤妻良母”的终极目标,男性意识到原本属于自己的利益即将被侵犯,继而内心便产生焦虑感,并对职业女性的看法有所改变。受固化的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上至统治阶级、知识分子,下至普通民众、寻常百姓,对于职业女性均颇有微词,甚至是奚落、质疑。苏雪林在安徽大学任教时,也曾受到来自男教师的冷嘲热讽。某次学校想派冯沅君和苏雪林以及另外两名教员一起到省政府请求拨发积欠经费,随即,便有一男性教师嬉笑着大声说道:“请女同事去当代表,我极赞成。这样经费一定下来的快些。”[3]尽管接受过高等教育,接触过西方文明,但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使得这些大学男教师在潜意识中,将对职业女性的偏见和歧视暴露无遗。“新女性”渴望重新获得人格和精神的自立,但在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却因为得不到社会认同,而满负伤痕。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社会的缩影。在普通民众看来,女性应修习女红、女德,重视妇言、妇容,尚无独立的工作能力,根本无法承担教学、科研的重任。社会对女教师群体的性别歧视犹如一把把利刃,直刺她们希望实现自我价值的心房,慷慨激昂的教学热情被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浇灭,她们心中该有多么酸楚与不安。
(二)国家政策的介入
相较于传统女性,民国时期的大学女教师更渴望获得精神与人格的双重独立。尽管妇女职业思潮从清末就已经出现,但因为国家政策的介入与导向,而致使她们在竭力追求独立的过程中,艰难前行。民国时期,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常常在“职业女性”与“贤妻良母”之间徘徊不定。大学女教师作为职业女性的典型代表,其发展趋势亦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民国初期《女子高等学校规程》的颁布,给渴求迈入高等教育的女性带来了希望。而后,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男女平等”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将男女经济平等作为党纲,“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依男女平等的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4]。1926年国民党二大妇女运动决议,将男女平等的政策落实到具体措施中:“根据同工同酬,保护母性和童工的原则,制定妇女劳动法;提出‘男女职业平等’、‘男女工资平等’的口号”[5]。在这一时期,大学女教师的数量有所增加。她们不仅肩负教书育人的要职,而且承担起琐碎的管理事务。但是,受男权统治的影响,1931年国民党四大重申,“女子教育必须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6]。这也就意味着,职业女性看似得到法律的庇护,事实上统治阶级却从未摒弃“贤妻良母”的政策取向,社会上引发了关于“母性主义”、“妇女回家”的激烈讨论,高校女教师的也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之一。国家政策是男权统治的象征,摇摆不定的政策取向,实则体现为两性之间利益分配的冲突。最初,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唤醒女性的职业意识,来促进社会的解放,增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当两性“角色丛”有所交叉,“新女性”的作用对父权的统治地位产生威胁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加以遏制,以确保原有统治地位不受侵犯。国民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犹豫不决,不仅消解了职业女性所追求的独立精神,而且使她们面临着职业与家事的两难选择。
(三)女性观念的异化
民国时期,女性的职业观念与价值认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然而由于大学女教师自主意识的薄弱,以及对“新女性”认同的匮乏,她们的自我观念出现异化,难以完成新旧角色间的转变。生活于男权社会的大学女教师,在有限的话语体系之中,其自我观念极易发生异化。民国时期,坚持自我中心、追求正义和权利的新潮流,让女教师获得了意识形态认同。但是由于她们无法摆脱三纲五常的束缚,无法突破三从四德的枷锁,反而使其加深了对“旧道德”下的女性的同情与认可。身为“新女性”,她们主张“自由、平等、服务社会”,渴望获得精神和经济上的独立。然而,大学女教师的拼搏努力依旧无法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却被迫承受着来自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长此以往,她们不免会产生对自我的怀疑,甚至分裂出对“新女性”价值定位的对立面。于是多数女师哀叹道“女人永远只是女人,除了作为人的玩具似的妻,和努力似的管家婆以外,没有其它的职业和地位”[7]。在职业角色的扮演过程中,女教师自主意识薄弱,极易受到父权统治思想变更的影响,进而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产生异化。她们的观念也就从“职业女性”退回到“贤妻良母”,从愤世嫉俗、不朽抗争到无奈接受、消极颓丧,脆弱的心灵早就不足以支撑那历经磨难后伤痕累累的躯体。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异化的自我观念,使其不仅无法彻底打破“旧女性”的枷锁,而且难以适应“新女性”的形象。于是,她们在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游移不定,在教学、管理和科研之间犹豫不决。虽然女教师作为新文化共同体中的一员,认同自由、平等的正义伦理,肯定个人的价值和权利;但作为女性,她们的性别意识和伦理观念,却使之无法真正冲突旧道德的牢笼,并且在争取自由解放的过程中做出妥协。
三、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角色冲突的调适
(一)独身主义
民国时期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与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妇女竭力追求经济上的独立和职业上的平等。在相对开化的社会风气下,独身主义被视为人格独立的体现,在女教员和女学生中盛行。坚持独身主义的大学女教师,一则为了促进院校的复苏和发展,鞠躬尽瘁,终身不婚,将自己奉献给教育事业。身为金陵女大首位中国女校长的吴贻芳,临危受命,担负起治校重任。吴先生终身未嫁,用她自己的话说“在等一个合适的人”,而在学生们的眼中,她却早已成为“嫁给”教育事业的“智慧女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王世静亦坚持独身主义,将自己奉献给华南,奉献给社会。在困难重重的社会背景下,她怀着对女子教育最赤诚的坚守,为华南筹资,争取特许状,实现了新旧华南的更替。二则因身负学校管理要职,且渴望逃避家事纷争,有限的时间精力和高标准的择偶要求,使她们只得面对孑身一人的结果。曾任北师大校长的杨荫榆,对爱情的憧憬却由于早年不幸的婚姻而化为泡影,以致最终被迫选择余生不婚,来化解家庭与事业之间的矛盾。受宗教性别观念的影响,教会大学中的女教师视“独身”为常态。在基督教新教看来,男女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和谐,而非控制压迫。作为民国时期女子教育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麦美德女士始终认为,婚姻意味着必须承担琐碎的家务劳动,继而也就失去自己的职业和独立的生活,因此,不婚就是对自由最后的坚守。在学生的眼中,麦美德就是一位坚定无畏的女性,甚至可称之为“女丈夫”。诸如此类的教会女教师仍不下少数,她们用坚毅的外壳紧紧地保护着自己,跨越荆棘、不惧牺牲,追求成功和自我实现。奉行独身主义的大学女教师,始终坚信“女子应该是社会的母亲,女子不仅是家庭的母亲”[8]。更有甚者,虽走入婚姻殿堂,但为效忠科研,只能牺牲为人母的权利,终生不育。她们虽然否定妇女的家庭角色,却力图通过扮演管理者、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职业角色来重塑“新女性”的形象,并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二)回归家庭
选择献身家庭的大学女教师可以分两类,一是出于对传统道德礼教的坚守,通过处理家务和照料子女来实现自身价值,从而间接实现社会价值。二是出于对婚姻、名誉的无奈,不得不离开教学岗位,退隐幕后,通过牺牲自己成就另一半的职业光环。留学归国的陈衡哲曾在胡适的力荐下,成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她才华横溢、叱咤讲坛,本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却۵因为生育而主动中断教学生涯。在她的心中,“家庭的事业是一件神圣可敬的事业,家庭是一个女性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场所”[9]。她肯定女性的家庭角色,认为女性靠自己的家庭劳动和抚育儿女,可以成为“孩子人格培养、智力增进、体格锻炼的操持者”[10],所以,为了全身心照顾亲人,她放弃了在学校教书的工作,回归到家庭中,一边养育三个孩子,一边抽空写作。甘愿做出这种选择的女教师,往往能够通过在家庭中的付出和所得来弥补内心的遗憾。无独有偶,“珞珈三女杰”之一的凌叔华也做出过同样的选择,但她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辛酸与无奈。凌叔华自幼擅长中西绘画,喜爱文学研究,也曾辛勤耕耘于武大的三尺讲台,却因为婚嫁文学院院长陈源而被迫辞职,只得以院长夫人的身份出入社交界。从她的文学作品集《女人》中可以看出,虽然她自己选择献身家庭,但她却号召女性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来自家庭和事业的双重精神压力,常常使部分大学女教师不堪重负,为了家庭的和谐美满,她们也只能被迫离开自己的职业,默默隐藏起心中的不甘。鉴于妇女的“天职”,无论是职业女性,还是传统妇女,“家事”始终在她们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当面对角色冲突时,部分大学女教师认为应先做好家事,再外出就业,“女子最好先将家政料理完美,为社会建筑一个坚固美好的基础,然后再出其所学,从事其它服务社会的工作”[11]。民国时期£,女性的职业生涯往往走入一个怪圈,她们经过坚韧不屈的奋斗,从家庭走向社会,最终又从社会回归家庭。
(三)协调兼顾
部分大学女教师既渴求扮演好家庭角色,又希望在职业上有所作为,为应对角色冲突,她们采取协调兼顾的调适措施,其中主要包括“超贤妻良母”和“夫妻配合”两种方式。“超贤妻良母”的推崇者认为,“‘贤妻’并不是指服从丈夫,而是要与丈夫共建美满的家庭,扶助丈夫的事业。‘良母’更无服从儿子的意思,而是要教育儿子,使之成为有用的国民”[12]。她们希望借助自身的能力、凭借自身的努力,顺利实现家庭和职业间身份的不断转换。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才女林徽因,虽然自幼接受西方教育,但面对着传统文化中女性须承担全部家事的原则,虽无可奈何却也无力更改,只能欣然接受。像林徽因一样,选择成为“超贤妻良母”的大学女教师,既有相夫教子的责任,又超越了女性困守家庭的限制;既反对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与无知,又主张拥有先进的知识和自强的能力;既担负起为妻、为母的家庭角色,又扮演好为人师表的职业角色。民国时期杰出的大学女教师在处理角色冲突时,自然也离不开丈夫的理解与支持。袁昌英和杨瑞六,俞庆棠和唐庆诒,冯沅君和陆侃如,他们凭借夫妻之间的同心协力,理解配合,著书立说,在学术界堪称佳话。男性主动分家务劳动,不仅能够清除女教师的后顾之忧,减轻女教师的心理负担,而且能够让她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教育教学中去。但在家庭和职业之间协调兼顾实属不易,选择此种方式的女教师更是凤毛麟角,“大抵都个性甚强,责任心甚重,天才又是比较高明的。因为她们不肯牺牲任何一方面,所以她们的内心冲突是特别强烈与深刻”[13]。她们既要付出千百倍的艰辛,又要承受巨大的负担和压力,但她们同样渴望在紧张的日程中获得片刻的休憩。除上述调适方法外,当时的学者还为职业女性提出晚婚少育、阶段性就业、劳动社会化、联家自治、兴办幼儿园、建设公共食堂等举措,希望通过缓解民国时期的大学女教师的工作和家务压力,使其既能保持“新女性”的精神状态,又能成为社会新潮流的掌舵者和引路人。
四、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角色冲突与调适的当代启示
(一)淡化传统性别观念,减轻女教师两难的心理负担
自古以来,“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致无论女性如何努力、如何优异,社会依旧按照“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标准来评判女性。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女教师,依然在被纲常伦理所束缚的社会中艰难生存,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因此,淡化传统性别观念,摒弃性别歧视,甚至是重建文化心理,对于实现男女平等至关重要。根据社会学家齐美尔所提出的“安全阀”理论,社会只有提供给成员宣泄不满情绪和敌对怨恨的制度,才能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因而,不仅要实现两性在经济上的平等,更要尊重两性在精神上的平等,对两性施以同等的人性关怀,给予女性舒缓心理压力的空间。在当今社会,随着男女平等思想逐渐地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看到数以万计的职业女性,为行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难以替代的杰出贡献。营造宽容、和谐、积极的社会氛围,给予女教师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更有利于发挥她们的潜力,展现她们的魅力。因此,只有整个社会对进入职业领域的女性予以包容,大学女教师的角色冲突才能得到有效调适,她们才会获得职业归属感,才能在适合自己的职业领域发光发热。
(二)稳定国家政策取向,给予女教师必要的社会支持
在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影响下,男性早已习惯以有利于自身的评价标准作为政策制定的唯一根据。从民国时期女子教育宗旨可以窥知,无论是效忠国家的“女国民”,还是温婉勤劳的“贤妻良母”,他们都将女性视为被动接受、缺乏主体意识的客体。及至南京国民政府在政策制定时,依旧一味地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进而使得“男女平等”的法案难以真正落实,以致引发“妇女回家”、“母性主义”的论争,职业女性难以教师成长在社会环境和职业环境中获得必要的政策支持。因此,将性别意识纳入到国家决策过程中,对于实现男女两性平等刻不容缓。鉴于两性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存在先天的差异,所以决策者在将“男女平等”的原则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法规中的时候,应当具备性别敏感和性别自觉,为女性弱势群体提供相关的政策优惠,促进两性在职业上的协调发展,以避免两性差距的扩大与加深。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优化幼儿园、小学、中学等公共机构的建设,为女教师的子女提供安全优质的照料与教育,以减轻她们的后顾之忧。国家政策的稳定和完善,不仅可以让大学女教师拥有安心工作的保障,更赋予她们奋斗在教育一线的决心和信心。同工同酬、晋升平等、待遇优厚等系列相关方案措施的出台,更可以使大学女教师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高深的学术科研领域。
(三)增强自我价值认知,提高女教师自身的承受能力
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出现与发展,冲破“男尊女卑”的藩篱,实现了女性的经济独立,展现了职业女性独有的魅力。但由于自我观念的异化,她们陷入角色冲突的困境之中,难以真正扮演好新女性的角色。因此,增强自我价值认知无疑是职业女性调适角色冲突的内在要求。献身家庭也好,独身主义也罢,职业女性只有清楚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明确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之后,才能在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获得职业幸福感。民国大学女教师矢志教育、效忠国家,筚路蓝缕、锐意进取,不断重获迎难而上的勇气,努力完成在不同角色之间的转换与调适。纵然在争取女性解放的道路上遇到诸多的波折与坎坷,但只要拥有了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才会笑对风雨、无畏荆棘。高校女教师也只有在清楚自我定位,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之后,才能在身为人母与学为人师、教育者与管理者、研究者与作家之间有所侧重。反观当下,大学女教师也只有确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才能凭借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获得自我效能感。大学女教师在应对角色冲突时,势必要提高对自我定位的要求,增强独立自主的精神意识,以更加坦然的心态和更加开阔的眼界,在不同角色间灵活转换,妥善处理矛盾和冲突。
(四)获得家庭理解帮助,舒缓女教师面临的角色压力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家庭能够给予女教师爱与归属的需要,因此家庭对她们的理解和帮助,成为女教师在面对角色冲突时最有利的后备力量。大学女教师只有在基本需求获得满足之后,方有条件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所以来自于家庭的温暖,将会成为她们心中那一抹明媚的阳光,为迷途的女教师照亮前进的方向。在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所面临双重角色冲突中,家庭与职业的角色间冲突成为困扰她们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女教师想要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在职业岗位上占有一席之地,摆脱对男性的依赖,获得真正的独立;另一方面,女教师受性别分工的影响,在生育之后,不得不承担起抚养子女的职责,难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纵观民国时期学术成果颇丰且家庭幸福美满的大学女师,她们的成功都离不开家庭的理解与帮助。夫妻之间不仅要在研究领域中产生共鸣,更要相互理解,家务合理分工,共同照料子女。只有大学女教员在家庭中的压力有所减轻,并且自身又具有在家庭与教学之间协调兼顾的能力,才能以更加轻松的状态投入到教育教学实践之中,投入到自己所热衷的研究领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已经身为人母的女教师可以完全将子女弃之不顾,女教师想要在学术与家庭中都有所成就,还需要她们不断提升自身的协调能力,合理分配花费在二者之间的时间,进而才能在两种不同的角色之间游刃转圜。
参考文献:
[1]董泽芳.论教师的角色冲突与调适[J].湖北社会科学,2010,(1):167.
[2]郭汾阳.女界旧踪[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68.
[3]苏雪林.苏雪林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355.
[4]鲍罗廷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Z].1924.
[5]国民党“二大”会议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记录(1926年1月16日)[A].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471.
[6]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494.
[7]庐隐.庐隐小说全集(下)[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784.
[8]潘丽珍.伊人宛在———守护精神[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8:26.
[9]眭浅予,罗宣.陈衡哲的母职观及其中西文化溯源[J].文史博览,2009,(8):25.
[10]陈衡哲.陈衡哲散文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115.
[11]宋孝璠.妻的责任[J].妇女杂志,1929,15(10):27.
[12]屠哲隐.贤妻良母的正义———为“贤妻良母”四字辩护[J].妇女杂志,1924,10(2):64.
[13]夏一雪.现代知识女性的角色困境与突围策略———以陈衡哲、袁昌英、林徽因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10,7(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