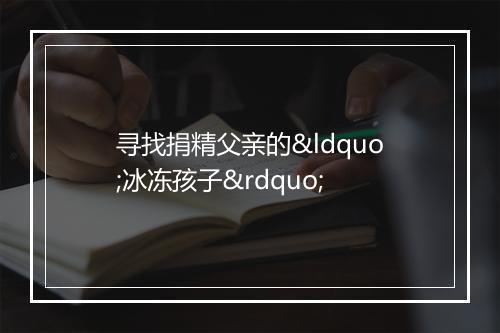寻找捐精父亲的“冰冻孩子”
现代生殖医学已经成功帮助数十万宝宝降临人世,现在他们长大了,对自己的身世提出疑问。来自捐赠精子的5个孩子讲述了他们的寻根之旅。
玛丽和蕾娜
他可能是超人,也可能是个超级讨厌的家伙;他们或许可以一起欢笑,或者只是沉默;他可能是个罪犯,也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许他早就死了――蕾娜的父亲。
28年前的某一天,他在一家诊所的一个杯子里留下精液,得到100马克后离开了。1986年冬,一对夫妻来到诊所。医生已经帮助过他们一次,他们抱着那个由陌生人的精子孕育出的婴儿说:“我们还想要一个这样的女孩。”
然而,这次“订购”却出了点问题:蕾娜并不是如同她的姐姐玛丽和父母一样是黑发,而是金发;家里所有人都从不长晒斑,只有蕾娜会在海滩上变成烤螃蟹一般的红色;所有人都是灰色或绿色的眼睛,只有蕾娜是蓝眼睛。5岁时她来到母亲面前问道:“妈妈,我是领养的吗?”“不,你是我的孩子。”母亲回答。她并没有撒谎。
父母给两个截然不同的孩子穿上同样的裤子和夹克,周日穿着同样的连衣裙去散步。姐姐玛丽戏谑蕾娜:“你肯定是邮递员的女儿!”如今蕾娜会大笑着反击:“你也是邮递员的女儿!”直到3年前,父母才向两个女儿坦承了真相:他们的父亲是不同的捐精者,蕾娜和玛丽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匿名捐精者
我从哪里来?谁是我的父亲?谁是我的兄弟姐妹?是什么组成了家庭――养育还是基因?对于在生育医学框架下出生的孩子,这些问题很难
回答。
数据显示,德国有10万多个深层冷冻的捐赠精子孕育出的孩子,即所谓的“冰冻孩子”。如今约1/50的孩子来自体外人工受精,每年1万多人,相当于一个小城的人口。新的生育医学中心不断成立。德国人想要越来越晚地建立家庭,生育能力却随着年龄增长急剧退化,目前有约1/10的夫妻丧失生育能力。如今寻求医学帮助的这代人,已经在学校学习了很多避孕常识,但对很多男人的糟糕精子质量和女人35岁以后直线下降的生育能力曲线了解甚少。
很多生育医学中心都挂着孩子的照片:甜美、可爱的小家伙,是抵达一段长长旅途终点的奖。励。在诊所网页上,可以看到最后终于得偿所愿的父母们的喜悦故事,却没有那些长大后提出疑问的孩子们的故事,例如蕾娜。
蕾娜在大学学习医学。在第七学期的人类基因学课上,她得知:绿色和灰色的眼睛基本不会生出蓝色眼睛的孩子。而她的母亲是绿色眼睛,父亲是灰色眼睛。一直存在的疑虑再次出现在她的心中:要么我是被领养的,要么我的母亲出轨了!蕾娜说:“我永远不想过问我父母的性生活,但是现在我给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告诉我真相,否则我自己去做亲子鉴定!”
如果蕾娜不逼迫她的父母,她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虽然《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每个孩子都有寻根权,有权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但是没有哪里比现代生育医学领域更容易规避这种权利。
精子捐赠不仅能帮助不育的男人和他们的妻子,也能帮助女同性恋和单身女人实现生子梦。此外,现代医学还能将一个卵子和一个精子放在皮氏培养皿中,植入另一个女人的子宫中。在比德国更加开放的国家,有些孩子有5个父母:捐精者,捐卵者,代孕妈妈,还有委托人,即希望得子的一对伴侣。
每年有远超1000名不孕德国女人使用捷克或西班牙女人的卵子生孩子,约500对夫妇寻找代孕母亲,这在德国还是非法的,在其他很多国家却早已合法。几周前,第一批由合法非商业渠道的胚胎捐赠孕育出的德国婴儿出生了:一对夫妻在人工受精成功后有了多余的胚芽,将之送给另一对不孕的夫妇。这是生殖医学时代的组合家庭,只是它的运作方式更加传统。即使卵子来自一个捷克女人,精子来自某位匿名的先生,但是长大后的孩子能看到大肚子的母亲和自己婴儿时期的照片,每个人都会觉得孩子长得像他们的父母。领养的孩子有时还有早期的童年记忆,或是和养父母有不同的肤色,而医生会为每位来到生育医学中心的顾客寻找最接近他们身高、体态、肤色和教育程度的捐精者。如果计划完美,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
接待玛丽和蕾娜父母的医生向他们发誓保守秘密。在慕尼黑一家ญ著名生殖医学诊所的主页上写着:“匿名捐精制使得每一对异捐精制夫妻都能完全以他们孩子的亲生父母自居,孩子在出生后自然而然就会作为他们的共同孩子载入民事登记处,可以完全杜绝孩子将来不得不面对感情冲突的情况发生。”
同时,保密也是对主治医生的一种保护,目前有不少诉讼都是针对培育“冰冻孩子”的医生的。去年,女大学生萨拉・皮恩科斯成功要求一位医生公开捐精数据,以便她可以找到自己的亲身父亲――一位同性恋教师。他们自那以后常常见面。然而,寻根权的前提是父母必须承认那段他们不愿启齿的历史。只有约10%的“冰冻孩子”知道自己出生的情况,仍有约三分之二的父母不想告诉他们的孩子事实。
凯文
沉默不是会让一切都变得更加简单吗?为何要让一个在家庭中很有安全感的孩子,被迫面对一个难以理解的真相“这个家以外的某个陌生人是你的父亲”呢?
我们可以指责凯文固执地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而不是轻松过好他的生活。有些“冰冻孩子”在经历了最初的迷惘之后就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一位34岁的经济学家说,他实际上只是担心,他的养父作为“传家宝”遗留给他的那块表会“在感情上贬值”。有些人却感受到深深的痛苦,甚至因此而抑郁,例如24岁的商务管理人员乌韦。但是乌韦也说,并不是真相让他受伤,而是多年的谎言。
家庭治疗师佩特拉・托恩呼吁家长早日澄清事实,最好是在孩子上幼儿园时就这样做,因为高年级的小学生就已经对自己有了固定认知,可能会对其身份认同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家族秘密酝酿的时间越长,毒性就越大。”佩特拉・托恩反对匿名捐献精子、卵子或胚胎。“如果孩子能够认识他们的捐精父亲,哪怕最后发现他并不友好,也是非常有益的。现实可让一个人建立起自己的和平世界,幻想却不行。”
胚胎捐赠
德国基尔法学教授、“胚胎捐赠网”法律专家莫妮卡・弗洛梅尔批评道,国外卵子捐献者都是在荷尔蒙的刺激下过度排卵的。“如果那些在成功完成人工受精之后仍有多余胚胎的夫妻,☑能够帮助不孕不育的夫妻,这比很多诊所开展的唯利是图的买卖要好得多。”
胚胎信息是匿名发布的,捐献者和接收家庭永远不会认识对方。孩子18岁之后才能知晓亲身父亲的名字,但是无法查到卵子捐献者的名字。弗洛梅尔指出:根据德国法律规定,孩子的母亲就是生他的那个女人。
“胚胎捐赠网”上希望获得一个胚胎的不孕者列表非常长,而捐赠者的列表非常短。只有少数夫妻想要和他们有100%血缘关系的孩子在一个陌生的家庭中长大,技术上可行的在社会上却让人难以接受。目前还是这样,但是几年后,胚胎捐赠就可能如同培养皿中的人工受精一样普遍了。1978年,英国出现第一例试管婴儿时,很多人都还对此感到害怕。一位《明星》杂志读者问道:“这些如同布谷鸟一样愿意在其他鸟的巢穴或是塑料容器中孵化出自己卵子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捐精也长期备受争议。1990年德国社民党还要求禁止这种生育方法,绿党也对此表示坚决拒绝。30岁的广告商米里亚姆1983年出生于一家大学医院。“那时我的母亲拜访了多位医生,但是没有人想帮助她。”她的母亲认为捐精令人尴尬,因此也从未对自己的女儿提起,她害怕孩子会被孤立和嘲笑。对此,慕尼黑德国青少年研究所的心理学家海因茨・金德勒说:“一个依靠买来的乌克兰卵子怀上宝宝的女人,怎能ค告诉自己的孩子:我购买了你?”
蕾娜起诉了那个培育出她的医生,要求其交出捐精者信息。她无论如何都想找到自己的生父。他的一张照片,一封邮件,和给予她基因的那个男人打个短短的电话,都能给予她莫大的帮助,当然最好是能在咖啡馆见上一面。“你是谁?”她会问他,“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你有家庭吗?你做什么工作?你的家庭中有哪些疾病?”蕾娜并不期望捐精者把她拥入怀中:“我现在并不需要一个父亲,我已经有一个了。”
这位父亲在她哭泣时安慰她,为她耐心地讲解数学题,在她想学骑马时给予她支持。他和她一起笑,她喜欢他的冷笑话。当她想中断大学学业时,他并没有骂她,而是静静地倾听她说话。圣诞节时,她为他写了一张卡片:“现在我在寻找自己的父亲,但是你一直都会是我的爸爸。”
以下是5个“冰冻孩子”的心声。
乌韦,24岁,商务管理人员,出生在柏林夏利特医院
家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秘密,只有我被蒙在鼓里。在我18岁生日那天,一个姨母告诉了我真相。我边哭边颤抖。我的父亲突然不再是我的父亲,直到今天我都没再和他说过话。他养育了我,教我分辨是非,告诉我不该撒谎。但是我的父母都做了些什么?我的人生本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有段时间我陷入抑郁的情绪中不能自拔。现在我好多了,但是我仍然一直都想知道,我来自哪里,我的金发和我小女儿的红发来自哪里。她是一个唇裂儿,出生时医生问我,家族中是否出现过同样的病例,而我不知道。我想亲自去一趟柏林夏利特医院,问问医生:捐精数据资料在哪里?但是当我问母亲,她是否支持我寻找亲身父亲时,她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
米里亚姆,30岁,广告商,出生于吉森大学医院
一年前,我的母亲哭了,只告诉我4个字:“人工受精。”这就像个巨大的玩笑。我一直都怀疑,我的父亲不是我的亲身父亲。当我直截了当地将之告诉我的母亲时,她一下子就崩溃了。那之后我给她写邮件:“为何你不把文件保存下来:我肯定是有价格的!”她告诉我,她非常害怕失去我。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恢复正常。我有个美好的童年,我的父亲像爱亲生孩子一样爱我。在寻找吉森大学医院的捐精者时,我认识了一个也在那里出生的女孩。她住在距离我很远的地方,照片上的她看起来和我并不像,而且和我完全不同,她的性格要冷静得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将自己的面颊黏膜涂片送到了一个基因数据库。几天前我们收到了结果: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我对我们的第一次见面非常期待,想知道她的动作、表情,她的怪癖,她是否也脊柱弯曲。有时我问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然而,找寻父亲的过程却仍然了无希望,我已经渐渐接受了自己永远都不会认识他的事实。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没有他就没有我。
凯文,24岁,音乐家,出生于埃森一家“试管婴儿”生育医学中心
我常常看着镜子,试图想象他的脸庞。但是我想象不出。我有他的眼睛,他的嘴唇吗?13岁时我得知,我是“人工”培育而成的。这个秘密让我心烦意乱。我觉得这样出生很可怕,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害怕,那个我在此之前都当作父亲的人,不会再爱我。在我们生活的小城市,不育仍然是一种禁忌,谈论起这事让我的父母很不自在。我不想伤害他们,因此我也保持沉默。但是现在我不想再对此不发一言了。我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带着父母的盼望出生的孩子,有可以让我自豪的勇敢父母。现在,我也感谢我的母亲很早就告诉我真相。我正在写一首歌,歌名叫“Novum”,这是我出生的诊所的名字。我希望能找到那位捐精者,希望自己不需要一辈子都询问:我的父亲是谁?我是谁?
玛丽:我总是在说,你是邮递员的孩子,因为你和我们家的其他人都完全不像!
蕾娜:是的,但是现在,你也是邮递员的孩子!
玛丽:真相改变了一切,我的身份突然变得不可靠,不确定了,虽然我一直都和爸爸很像。
蕾娜:我们的母亲总是对你说:你像你的父亲。三年前得知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孩子时,你非常震惊。我当时问☁的是:那么,医生是我的父亲吗?我能见他吗?当母亲说起有两个匿名的捐精者时,我几近昏厥。
玛丽:现在我第二次怀孕了,非常想找到我的父亲,让我的人生拼图完整。当然这只是出于兴趣,我并不需要可以依靠的肩膀。也许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不想打扰他的生活。两个完全的陌生人突然相互拥抱什么的,太老一套了。
蕾娜:但是如果能好好和他达成理解,将会是巨大的幸福。
玛丽:最初几年,捐精者大部分是医学院学生,因此我成为医生可能并不是个偶然。我们将自己的唾液样本送到基因数据库。结果是,我可能有来自巴基斯坦和叙利亚的血统。
蕾娜:而我是完全的欧洲血统,这一点也不酷!而且我还得知:我有个同母异父的姐妹!
玛丽:是的,就是我!现在至少能确定,我们俩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